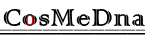第五篇 我的二哥
二哥名曰健,是我们姊妹四个当中长得最英俊、字写的最好、数学学的最棒的一个。可能是由于他长得实在帅加之老爸特别喜爱女孩子的缘故,从小父亲就把他当成女孩子来打扮。
现在家里还有一张拍摄于上世纪1966年大哥二哥一前一后站立着的黑白照片;二哥在前,脚穿花布鞋、身着类似于现在女棒球选手穿着的连腿短裙裤,头发集成小辫在头顶扎着个蝴蝶结,双手装在短裙裤裤兜里,面不露笑的一双大眼睛紧盯着前方的照相机镜头;二哥的身后站立着当时已经四岁、脚穿球鞋,身穿双色背带裤、胸前别着一枚长方形小型毛主席像章,虎头虎脑望着照相机镜头的大哥,黑白照片的左上角有三个影印上去的白色字迹:小兄弟。
小时候记得我们工程局经常停水,又没有水井。只要唯一的一条井水管停水,我们兄弟们就必要在放学后,一人拿着扁担或竹竿,一人提着空着的用白铁皮箍做的直径大约有四十公分的铁皮水桶,去四五里地以外的北大分校653去抬水回来吃。(当时统叫代号653,关于这个653,大家现在可以百度一下《大学轶事 “三线”往事:汉中有个“653”》还可以百度一下原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王义遒先生的回忆文章《褒水连城的记忆----写在北京大学汉中分校成立50周年之际》中,对连城山、对653的描述;这个叫653的北大分校后来改名陕西工学院,现在又叫陕西理工大学北校区;据说这个我们儿时常常爬上去游玩的叫做连城山的山峰就是诗仙李白在《蜀道难》中“连峰去天不盈尺”一句中的连峰。)
记得抬水最多的是我和二哥,一般我走在前面,他在后面。有时候我走着走着会突然发现肩头一下子轻松些了,回头一看,是二哥将偌大的满桶水有意挪在靠近他胸前的地方,那时候觉得二哥最体贴我,以后我大约就开始不喊二哥而改口叫好哥哥啦!
写到我的好哥哥,就让我想起他上小学的趣事、糗事,只要我一想起就忍不住想要一个人偷偷地狂笑。
这些让我想起好笑的事情是这样子的:
关于我二哥至今让我印象最深仍想哈哈大笑的事情有这么两件:
第一件-----
那时候我应该已经读三年级了,二哥应该读四年级。水利人家的土胚房一般都是筒子结构,前居室后厨房,而且房间也不大,面积大约只有四十到五十平米左右,一家六口就蜗居在那样简易的环境中。印象那会儿,家里就两张大床,父母一张在靠近厨房门的位置,屋中间用铁丝横拉一道、然后用废旧床单做成隔帘,我们兄妹四人一张大床在布帘的这边,通常都是大哥二哥分睡两头一个被筒,我和妹妹分睡两头一个被筒。(因为房顶是人字型铺放的油毛毡,我们都习惯叫油毛毡房,新中国最早的房建规范中防水工序中的三油两毡就说的是我们那种房顶防水吧!)
那时候都是用的公共露天厕所,一到夏天粪坑的臭气能把人熏晕、厕所里的地上经常是蠕动着的白色蛆虫;厕所墙根还有好多被单位撒过66粉毒死的蛆虫和黑色的蛆壳。可以想见,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为了祖国水电建设做出贡献的这些我的父母辈们生活、居家的条件有多苦。
由于公共厕所一般都离家属院很远,因此一般秋冬季,所有人家都在夜间配备尿屎盆,第二天一大早,居民们一致统一的行动就是相互打着招呼,一起去往公厕倒尿屎盆!
就是前面说到的二哥四年级的那个冬天,有一天夜里我睡得正香,就听见很大的哗啦哗啦的声音,刚迷迷糊糊睁开眼睛的时候还以为下雨,仔细一看,是二哥闭着眼睛在撒尿,让我好笑的是他没有撒在尿屎盆里,而是将父亲雨天工作时穿的长筒胶鞋当成了尿盆,居然就把憋了一夜的童子尿撒在了那双无辜的雨鞋里!
哈哈哈哈哈哈哈!!!
第二件----
仅管二哥是我和妹妹的二哥,但他上小学的时候鼻涕“流过黄河”的情况远超过我们而且还是最常见的。(我们当时的小朋友都把谁鼻涕流过嘴巴叫“流过黄河”),二哥鼻涕多也还不算好笑,最好笑的就是他有时候与他的同伴还有带领院里我们这些比他小的玩伴们,玩“补锅”(一种我们童年时用和好的黄泥巴做成方型、圆型中空的翻转过来往地下一摔被气流将原先密实的底盖冲开一个小窟窿、随即发出“啪”一声的游戏,情状就想谁家的锅子烂了,而后再重新糅合二次再来、类似于补锅,因之叫补锅)或者玩弹溜溜时(弹溜溜就是当时我们玩的弹玻璃球,就是沿一条直线,间隔两米左右挖几个拳头大小的小坑,在起始洞口由上家弹出自己的首枚玻璃球、进洞为赢,对方要给自己一枚玻璃球;而若上家弹出的玻璃球不曾进洞,则下家就用自己的玻璃球弹撞上家那枚玻璃球,如果恰好将上家那枚玻璃球撞进坑里,则上家得把自己先前未弹进洞那枚玻璃球送给下家,以此类推。弹溜溜有的地方叫弹珠,溜溜有玻璃的、也有陶瓷的、玻璃的还有花瓣的,这种花瓣的多是谁偷拿家里面的玻璃跳棋棋子来玩的,若是谁有几个花瓣的溜溜,那时候可是神奇的不得了)就在玩这些游戏的过程中,我就经常看见二哥边吸溜吸溜的将本已过了“黄河”的鼻涕用力吸回去,边极其认真的用劲摔他的“锅”、或者趴在地上不顾将地上的黄土、灰尘用劲吸鼻涕的时候吸进鼻腔,而眼盯前方,拇指和食指做成端酒杯状、将夹在两指之间的溜溜用力弹射出去,随着玻璃球进洞的欢呼、或是未进的惆怅,二哥就忘了将流出的清鼻涕吸进去,而是直接用衣袖横过嘴巴,用力的一抹,袖口便有一道泛着银白光芒的鼻涕印痕,久而久之,我观察到他的两只袖口有点像集市上剃头老头的荡刀布、又硬又光。每次我一看到他用袖子抹鼻涕,我都会忍俊不住的哈哈大笑,彷如此刻敲字到这里,我就一个人对着显示屏嘿嘿的傻笑。(二哥这一奇葩动作甚至到他上初一时都还是保留节目)
现在想起二哥,也不光只有他的这些好笑的糗事,还有一两件有关于我俩恩恩怨怨的事情,让我记忆犹新、难以忘怀!
第一件----
记得有一次是个周末,我的小伙伴们本来约好要一起去爬连城山玩,可是刚睡起来,母亲就叫我和二哥去653抬水。(前一天晚上井水管还有水,这周末第一早上突然停水)我极不情愿的嘟嘟朗朗地拿着竹竿跟着提着白铁皮水桶的二哥往653方向走,越走我越来气,就对二哥说:“二哥,你看咱妈像不像一个地主老太婆,一天到晚就知道压榨咱们!”谁知道二哥一听完就奸笑着说:“哈哈,好啊,你敢把咱妈说成是地主老太婆,看我回去不告诉妈才怪!”我一听二哥这样说,也有点紧张,就央求二哥不要告诉母亲,二哥嘻嘻讪笑着对我说“行行行,不告诉,不告诉。”可是他最终还是回去把我说母亲的话告诉给了母亲和大哥,母亲和大哥倒也没怎么说我,只是有时候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母亲会把我这句话拿到桌面上逗我,弄得我好几次都有点不敢看母亲的眼睛。
第二件----
也许是上次被二哥当面答应好好的又背后告了我的密,这以后我总觉得这个我一直认为是好哥哥的有点不够意思。于是便好像出现了不和谐,而且这种不和谐还有增无减。可能正是因为不和谐量变达到了质变的程度,有一次我现在忘了是因为什么,反正觉得当时被二哥欺负了,心里憋屈得很,想着要找个机会,报复二哥一下。终于在一个午后我放学回去看到二哥在厨房帮着母亲烧火拉风箱(那时候我们院里几乎每家人都烧柴火或是散煤做饭,要用木头做的风箱煽火)于是我放下书包,蹑手蹑脚的走到二哥身后,趁他不注意,擂起我的右拳,用当时我们小朋友最爱用的一句话,那就是使出了浑身吃奶的劲,将我那只小拳头硬生生砸在了二哥的后心上。随着“啊哦”的一声惨叫,我此刻都似乎还能听到二哥当年惨叫的声音......
我见状撒丫子就往屋外跑,耳后传来母亲对我的责骂声,这时候已经觉得二哥飞身站起,急匆匆追了出来,他边追我边喊我的外号“三刀客,你给我站住,别让我逮到你,逮到你非打死你不可!”我哪里敢停,沿着我家对面那两排平房之间的胡同没命的奔跑,这个时候就觉得脑后一阵微风、接着一个铁件落地的清脆响声,我边跑边稍稍回头一看,不觉浑身都冒出冷汗来。
原来二哥看我已经跑远他实在无法追上,就将别人放在院门口的一张铲煤的方型带把铁铲,像投掷标枪一样罩我后脑甩了过来。也幸亏我早就跑远了,但凡慢一点,就是不砸在后脑也会砸在脚跟,现在我都还能想起那个铁铲落地的清脆响声和砸出的深坑,可见那一次我那一拳是真的把二哥打疼了!其实就在我砸完那拳心恨已结的瞬间,我就开始心疼、担心起我的好哥哥来,我真的已经开始深深地责备自己,我一直在心里说:二哥,对不起!二哥,对不起!
这些都是我和二哥小时候的往事,当然无论美好的或者不快的往事绝不止这么多,但给我印象较深的差不多就是这些。
后来二哥在1982年招工参加工作后依然对我和妹妹还是很好!
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已经是个初中生了,那时候也学着同学开始集邮,应该是1984年,我就要初中毕业的时候,二哥那时候已经在陕西省安康火石岩电站工作,有一次他探家回来,就给我买了本集邮册,要知道那时候能有个精美的集邮册放邮票也是能在同学们面前小拽一下的。因此别提当时我的心里有多高兴。
记得二哥还用他镌秀的钢笔字给我题了:方寸小世界,集邮大空间----祝吾弟学业进步、二哥等字样。那本小小的集邮册我至今还保留着。
这之后,我的二哥受够了我们这种大型国营水电施工企业,对人性、对个性、以及对人权的重重挤压,一生气办了辞职,自己到外面发展,现在也是广州一家咨询公司四川自贡分公司的老总了。
写至此,似乎暂时可以结束我对二哥的追忆,但不论我们相隔多远,不论小的时候我们之间发生过什么,我的二哥永永远远都是我的好哥哥,就让我在这秋雨霏迷的粤西吴川小地,在这只听见雨水滴答而再无其他声音的乡野一隅,遥祝我的好哥哥一家人时时安康,处处顺心!
2018.8.14
注:“三刀客”实乃河南邓州家乡话,客字实际读起来是发kai的音,意即“土匪”的意思;上世纪三十四年代,我的家乡常闹土匪,有人就管土匪叫“刀客”,我小时候比较赖皮,就被哥哥们给我起了这个外号。2018.8.15上午于粤西吴川
版权声明:CosMeDna所有作品(图文、音视频)均由用户自行上传分享,仅供网友学习交流。若您的权利被侵害,请联系删除!
本文链接://www.cosmedna.com/article/91789122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