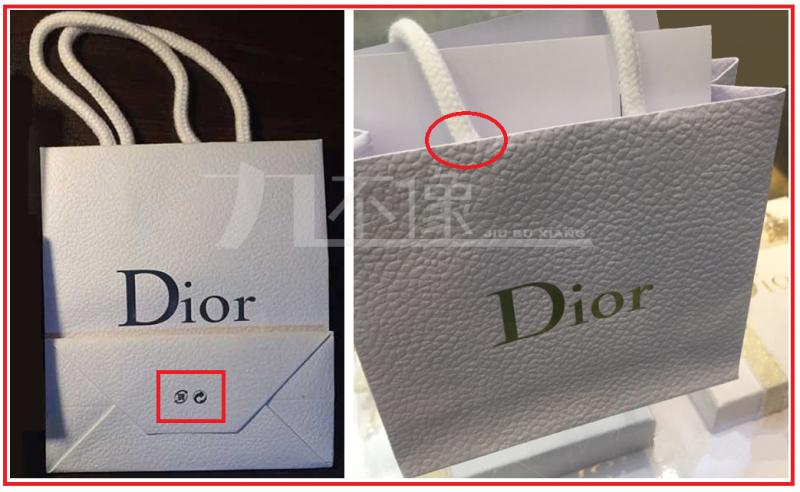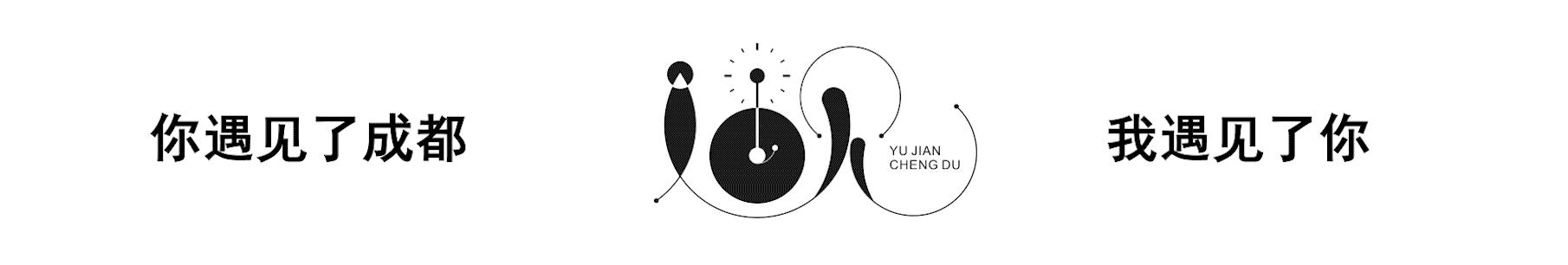考古暨历史语言通讯

作者 京都静源 教授/文学博士
第三、断代史研究
1654年,卫匡国教士出版了《鞑靼战争史》(《De belllo Tartarice Historia》)一书。这部在西方汉学史上有重大影响的研究清代初期历史的名作,是当时西方汉学界热衷于所谓“鞑靼史”研究的一个高峰。此书出版后,很快被译成西方各种文字出版。据此书出版约三百年后,又被译成日文出版。足见此书在东西方汉学界影响之大。在当时同类题材的研究著作,如,1671年,格瑞斯朗教士(Adrien Greslon)出版了《鞑靼人支配下的中国史》(《Histo irede la Chine sous la domination des Tartares》)一书。1777年,刘应教士(Le P. Cl aude Visdelou)的《鞑靼史》(《Histoire des Tartares》)一书也正式出版。等等。
在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上,1658年,卫匡国教士出版了《中国上古史》(《Sinicae Historiae Decas prima》)一书。如果说他对鞑靼史的研究反映了他对当时中国现实的关心的话,他的中国上古史研究则说明了作为一名汉学家的职业中国观和研究核心所在。关于此书,卫匡国教士的最为重大的学术贡献是:他在西方汉学界比较早地肯定了中国上古史中的真实的历史记录至少开始于公元前2952年。而当时依据《圣经》的记录,人类社会的历史开始于公元前2365年。换句话说,他以中国上古史的真实和永远来否定《圣经》中的创世说。
1775年,在西方汉学史上声名赫赫的那个钱德明教士又出版了一部震惊当时学界的名著《中 国古史研究》一书。这部史学著作实在是汉学史值得大书特书的一部名著!在来华传教之前 就十分精通西方传统历史学理论的钱德明教士,在此书中,他认为:在古代中国的历史中, 因为使用了在当时的时代里是极为科学的干支纪年法,这使发生在上古时代的有关夏、商、 周王朝的一切历史活动,都可以在天文学上得到科学性的年代验证,并由此为考证古史的产 生年代和真伪问题提供了极为难得的力证。在当时的西方汉学界,没有谁会对钱德明教士书 中的论证表示不满,并由此怀疑他的结论的可靠性。但是,在我看来:作思想史研究的人感 兴致的不是论著自身的圆满性问题,而是在论著中所表达出的一种思想的学术价值和时代意 义等问题。这部著作极有学术价值,除了他的史学思想和史学研究方法之外,还在于以下二 点原因:其一,此书解决了当时困扰在西方汉学家心中的中国文明的由来问题。那时有所谓 中国文明来自古希腊说、来自古巴比伦说、来自埃及说、来自美洲说,来自欧洲说等等。这 些历史学家们的学说完全无视中国古代的历史记录!现在经钱德明教士研究考证,古代中国 的史书作为信史对中国文明的由来问题进行了最好地说明和回答。其二,此书首次从中找出 一条和《圣经》的创世时间记录不一致的古代中国历史的发展线索。这是和当时的传教士史学研究传统不一致的,因而也是最值得注意的地方。当钱德明教士正在研究上古中国史籍记录的真伪性问题时,清代的历史学家们已经开始了考据学的研究。同样的工作,不同的方法, 得出的结论却不尽一致!这真是极有意义的一个对比。和钱德明教士的中国古代史研究水准 几乎不相上下的那个同样也是大名鼎鼎的宋君荣教士,在他死后的1791年和1814年,他研究中古史的遗著《大唐史纲》一书也正式出版。
1857年,符拉包沃斯基教士(M. Xраповицкий)的《明末李自成起义和北京事件》(《События в Пекне при паденин Минскои династии,труды Росс.Дух.Мисс.В Пекине》)一书也正式出版。
断代史研究,在早期西方汉学史上更多的是对上古史、蒙古史、元代史的研究。而对汉代、 唐代、宋代史的研究则是本世纪早期现代汉学史上的重点。但是早期西方汉学史上的断代史 研究,后来多形成独立的蒙古学、中国问题研究等研究课题,有脱离中国通史体系中的断代 史研究倾向。
第四、专题研究
专题研究的内容也是很广的。如,年历学的研究、外交史的研究、地理学的研究、交通史的 研究、人物传记的研究、文化史的研究等等。
如,年历学的研究,传教士们注意到了中国有着特殊的历史纪年方法——而这一纪年方法的 成立基础是中国古代的天文学。钱德明教士曾说:“作为古代中国的政治学的第一对象,中 国人的政治要点是他们的天文学。为何这么说呢?因为在他们的观念中,天文学并非是个历 法的问题,如果不能准确地计算的话,某一古代帝国的繁荣就将因此而失去。”《L ettres Edifiantes et Curieuses Ecrites des Missions Etrangeres par Quelques Miss ionnaires de la Compagnie de Jesus de la Chine et des Indes Orientales》,由日文 本《エイズス会士中国书简集》译出。平凡社,昭和45年。
这也就是古代中国人的天人感应论思想的一个有力证据。因此之故,传教士们在研究古代中 国的历史时,首先要明白中国的历史年代和西方的公元制度的对应关系。这就客观上促进了 对年历学的研究。但只有钱德明教士这位优秀的汉学大师才独具慧眼地发现了年历学的政治 含义。
1687年出版了柏应理教士研究古代中国年历学的工具书《中国六十甲子纪年表》(《Tabula Chronologica Monarchiae Sinicae Juxta Cyclos LX》)。由柏应理教士的私人学生、作为医生的门泽尔博士编纂的《中国历史年表》(《Kurtze Chinesicheo der Zeit Register al ler Chinesischer Kayser》)一书,在17世纪的晚期也得到正式出版。1728年,傅圣泽教士研究中国古代年历学的著作《中国年历研究》(《Tabula Chronologica Historiae Sinic ae Connexa cum cyclo qui vulgo Kia tse Dicitur》)一书也正式出版。
对于年历学的研究,直到今天,在中国历史学界仍是一个少有人问津的领域。作为20世纪年历学研究两大权威学者的陈垣和董作宾,对中国古代历史和文明的分期和断代、历法、天文学、数学等学科作出了空前的解答。但是如果没有这两位史学大师的话,我们是否要向西方学术界去请教中国古代历史和文明的准确的发展时间线索呢?
作为专题研究的一个内容,1828年出版了比丘林教士所作的《清初中央政府和西藏》(《Opi sanie Tibetav Uyneshiem ego Sostoianii》)一书。在这部研究西藏和清政府之关系的著作中,对西藏宗教和清政府之关系的研究是该书的特色之一,并由此成为现代西方汉学界、藏学界研究进行此类研究的先驱。
中国外交史和中外交通史的研究,一直是传教士们汉学研究传统中的弱项。1758年,罗迪格特教士所作的《历史新探:中国、日本及印度支那等国古史的研究》一书正式出版,在本书中,罗迪格特教士对中国、日本、印度支那等亚洲国家的历史发展进行比较性研究,特别是对上述三国和各自周边国家的历史关系的分析和说明,开启了以后中国外交史、中外交通史研究的先河。
人物传记的研究,如,1697年出版的由白晋教士所作的《康熙大帝传》一书。此书曾有英文、日文等文字译本出版。1829年出版的由比丘林教士所作的《成吉思汗家族早期历史的研究》一书。1851年出版的由德国汉学家郭士立教士(Karl Friedrich Gutzlaff)所作的《道光皇帝的生平》(《The Life of Taou Kwang late Emperor of China》)一书。等等。
文化史的研究,如,1770年出版的由马若瑟教士所作的《书经时代以前中国古代神话和历史的研究》一书。此书和钱德明教士的《中国古史研究》一书有若干相合之处:①这两部著作都以中国上古史为研究中心,利用的史料也以先秦时代的经、史、诸子著作为主。②此二人的基础史学思想表现在研究中国上古史事时有一个最为基本的共同点:以史籍、神话、传说证明中国远古社会的发展史。③作为基督教教义的一个体现,此两部著作都或多或少的注意到了所谓《圣经》创世说在中国古籍中的证据问题。
其中,对于中国人种和中国文化的由来问题,法兰西科学院的院士顾根斯(Joseph de Gui gens)1757年发表的《中国人种和文化起源于古代埃及说》(《Memoire dans lequel on pro uve que les Chinois sont une colomie Egyptienne》)一文中,提出怪说:中国人种和中国古代文化来源于古代埃及说。作为法兰西科学院的院士,顾根斯此说一出就引起了汉学界极大的骚动。他的理由只是:古代汉字和古代埃及文字,作为象形文字,在其具体的表现上有其相似性。有关古代汉字和古代埃及文字的相似性问题,中国学术界一直无人了解此事。更不要说介绍和研究论文的发表了。这实在是让人倍感遗憾的事情。在中国学者看来,作为象形文字的汉字,是中国文化背景下产生的专利。伏牺画卦和仓颉造字是中国文化赖以成立的基础。这使古今文字学家们对古代汉字和古代埃及文字的相似性问题一直不感兴趣。也难怪,中国至今只曾有过一位古代埃及学家,他就是著名的考古学家夏鼐博士。但是,夏鼐博士又是以古代埃及考古学为专攻,以我之所知,他对古代埃及文字的研究并没有兴趣。但是,作为西方汉学史上有关中国文明诞生之源头的研究,“中国人种和中国古代文化来源于古代埃及说”是个十分重要的观点。在此,我对古代埃及文字略作介绍,才能使大家明白此说成立的基础和意义。
作为象形文字,在文字体系上最为完整、历史最为久远、内容最有研究价值的是古代汉字和 古代埃及文字。但两者文字有不少字形和意义完全相同。如,“丙”、“丁”、“己”、“子”等干支字,古代埃及文字和汉字的古文为完全一样的。类似的字,至今已发现约有数百字。再如,意义完全相同而部分字形一样的,如,“山”、“水”、“刀”、“雨”等字。古代埃及文字和汉字的古文部分字形一样。这样的字,至今也已发现约有数百字。除此之外就是字形完全不同的字。特别说明:以上引文参考了《古代汉字和古代埃及文字同源考》 (《De unitate originis litterarum Sinicarum et Aegyptiacarum》)一书。板津七三郎《古代汉字和古代埃及文字同源考》,岗书院,昭和八年。当然,既然存在相同、相近的字,就可以使用六书体系来分析和研究古代埃及文字。这样一来,既可以发现象形文字的基本造字规律,又可以利用古代埃及文字来协助破解至今文意不明的甲骨文字。当然,我在此引用以上几个字是因为有件文化史上的大问题至今没有解决。即,干支的由来问题。在古代埃及文字中出现的干支、以及在古代巴比伦文化中出现的干支,从字形到读音是完全一致的。在对干支的起源进行考证之前,没有理由断定干支起源于中国。也不能肯定干支起源于古代埃及、古代巴比伦。轻率作出结论是不可取的。
在18世纪的西方汉学界,所能见到的中国古代文字当是金文、篆文、古文三者。到了19世纪末才发现甲骨文字,以甲骨文字和古代埃及文字进行比较研究,才是象形文字研究的开 始。而当时的顾根斯院士居然能提出此说,实在让人敬佩!在没有发现甲骨文字之前,金文、篆文、古文三者的历史年代当然后于古代埃及文字。这也难怪西方汉学家们要提出“中国人种和中国古代文化来源于古代埃及说”了。但是,顾根斯院士的研究专长是古代叙利亚语和古代印度语,他的汉语和汉学研究只是作为他进行东方学研究活动中的一个业余爱好。有关这类问题的研究,后来又有来自古代巴比伦说、古代美洲说等等。当时就遭到了俄罗斯帝国比丘林教士的著文反对。
第三节中国思想史研究
第一、儒家经典的翻译和出版
1593年,利玛窦教士等人将《四书》编译成拉丁文、以《Tetrabiblion Sinense de Moribus》作为书名,正式出版。1626年,金尼阁教士翻译出版了《易经》。据说,此书是在中国杭州印刷的。因为当时金尼阁教士曾在杭州建立过印刷所,用来印刷《圣经》和传教士们所作的中文著作。我至今尚没有见到这一原始版本的全貌。在中国学术界,甚至有不少学者相信金尼阁教士利用杭州的印刷所翻译并刊行了著名的《诗》、《书》、《礼》、《易》、《春秋》“五经”全文。1662年,由殷铎泽教士和郭纳德教士合译的儒家经典《大学》,以《 Sapienttia Sinica》作为书名,正式出版。1667年,殷铎泽教士和郭纳德教士把《中庸》 以《Sinarum Scientia Politico Moralis》为书名,合译出版。其中,殷铎泽教士多次蒙康熙皇帝接见,他的汉学造诣和汉学著作对于基督教在清初的发展有他人所不能及的贡献的,也奠定了意大利汉学发展的基本走向。1687年,柏应理教士出版了由他编译的《四书》拉丁文译本,书名定为《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我在本书第一编第三章第五节中已经详细地说明过了这一版本的由来问题。方豪博士在《十七、八世纪来华西人对我国经籍之研究》中曾评述此书说:“惟《孟子》未译,故称以“西文四书”,实不甚妥。亦名《汉学拉译》。方豪《十七、八世纪来华西人对我国经籍之研究》,见《方豪六十自定稿》,学生书局,1969年。
同年,格瑞白尔教士(Grueber)出版了一部研究儒家思想的文集《中国思想研究手记》(《No tizie Varie dell Imperio della China》)一书。
第二、易学研究
冯秉正教士,也曾翻译了《易经》,但没有正式出版。1715年,白晋教士和傅圣泽教士二人奉康熙皇帝之命开始学习《易经》。方豪博士在那三大部著名的《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一书中公布了在梵帝冈图书馆中保存的与此有关的文献。方豪博士《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一书中又说:“梵帝冈图书馆藏有西士研究《易经》的抄本十四种,多与白晋有关。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台中光启出版社,1973年。这“ 西士研究《易经》的抄本十四种”书名如下:①《易考》。②《易稿》。③《易钥》。④ 《〈易经〉一》。⑤《易引原稿》。⑥《易学外篇》。⑦《太极略说》。⑧《〈易经〉总说 稿》。⑨《释“先天未变”》。10《大易原意内篇》。11《据“古经”考“天象不均齐”》。12《“天象不均齐”考“古经”籍解》。13《总论布列类〈洛书〉等方 图法》。14《易考》。(与①同名而异实)除此之外,有关《易经》研究的手稿本,据我之浅见所知,还有四种未刊的稿本存在:15《Idea Generalis Doctrinae Iibri I Kin g》。16《Ess D'Introduction Preliminaire a I'Intelligence des King》中的《I King》部分内容。17《周易原指探》。18《琐言分类》。以上手稿分别藏在法国王 家图书馆、意大利的罗马、梵帝冈图书馆等地。
研究传教士为何热衷于易学研究,这实在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自西方古代社会以来,有一 种研究《圣经》中的单词字母所含数字意义的学问,是一种由数印证《圣经》内容的研究方 法,即所谓的神数学。这种神数学和中国古代易学中的“极数知来”的象数易学观念有极为 相似之处。而《易经》和《圣经》之间至少有以下三点在本质上的一致:①二者文中都有对 天、帝、理、性的阐述。②二者在形式上都有由数到象(内容)的理论基础。③二者都具有神 秘主义的表现和思想实质。由于以上三个原因。造成传教士们在研究中国古代儒家经典时 ,对《易经》情有独钟的现象。当然把易学作为一种独特的象学思想来进行研究,这是现在才开始的事情。东西方的易学家们也许永远不能理解象学思想在《周易》发生学中的意义和价值,西方几百年、东方近千年之久的易学思想研究史都在“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迷境中徘徊着。
1728年来华的查瑞梅教士(Alexandre de la Charme)后来曾以法文翻译《诗经》和《仪礼》 出版。1770年,宋君荣教士翻译的《书经》,以《Chou King》作为书名正式出版。1861年 开始,利雅格教士出版了他的翻译的古代经学著作的多卷本英文著作《中国经典》一书。1829年,比丘林教士曾把《三字经》译成俄文出版。1780年,列奥尼切也夫教士把《大学》和 《中庸》分别以《Да Xие то естъ учение Великое》和《Джун юо естъ закон непреложный》作为书名,正式出版 。
方豪博士又在《十七、八世纪来华西人对我国经籍之研究》一文中,以十点理由说明了来华 传教士研究儒家经学思想的原因,如下:“一、由于传教心之热也。二、由于国人对经籍研 究之注意也。三、由于汉文之精也。四、由于学侣之多也。五、由于反对者之攻击也。六、 由于中国士大夫之欢迎也。七、由于帝王提唱之力也。八、由于教士生活之恬静也。九、由 于教内对中国礼仪问题而兴起之长期辩论也。十、由于教士以中国为第二祖国也。”方豪《十七、八世纪来华西人对我国经籍之研究》,见《方豪六十自定稿》,学生书局,1969年。
以上十点中最本质一点是“由于教内对中国礼仪问题而兴起之长期辩论也”。这是汉学在西 方社会得以发达的原因。对儒学的研究,特别是对易学的研究组成了传教士们的对汉学思想 研究的核心。
第三、儒家思想研究
1678年,斯巴发利教士写成一书,但直到1910年才正式出版。布罗夫博士曾在《俄罗斯的中国哲学研究》一文中注释:“它第一次出版是在1910年СпаФарий. Опи сани е первыя части Вселенныя именуемой Азии В нейже состоит Китайское яосударство спрочими е гогороды и провинции.Казанъ.1910. LVI。 271c.”Владилен Г.Буров 《Изуче ние кнтайской Философии в СССР》,见《汉学研究通讯》,第14 卷第4期。这本书也有关于中国宗教与哲学;孔子学说等的知识。它虽然没有出版, 但是副本流传颇广,包括国内与国外。
1701年4月,哲学家莱布尼兹博士把他的《论二进制算术》一文寄给远在中国传教的友人白晋教士。当年的11月,白晋教士回信寄给他两张图,即:《六十四卦次序图》和《六十四卦方位图》,这就是中国古代易学理论中最为有名的六十四卦的次序图和方位图。莱布尼兹博士本人立刻发现图中的阴阳爻表示方法和他本人的《论二进制算术》一文中的理论出奇一致!由此揭开了争论至今的《论二进制算术》和白晋教士寄给他两张图何者为先的问题的序曲 。
莱布尼兹博士在致白晋教士的信说:“再提到大涵的重要问题吧!这就是我的二元算术和伏 牺易图的关系问题,人们都知道伏牺是中国古代的君主,世界有名的哲学家,和中华帝国, 东洋科学的创立者。这个易图可以说是现存科学之最古的纪念物。然而这种科学,依我所见,虽为四千年以上的古物,数千年来却没人了解他的意义。这是不可思议的。他和我的新算术完全一致,当大师正努力理解这个记号的时候,我依大涵便能给他以适当的解答。我可以自白的,要是我没有发明二元算术,则此六十四卦的体系,即为伏牺易图,耗费了许多时间,也不会明白的吧。我之发明新算术,是在二十年前,我认为以‘0’与‘1’表示的算术,较之从来所有的更进于完全之域,是有不可思议的效果的。引自朱谦之《中国思想对于欧洲文化之影响》,商务印书馆,1940年。
在现代中西易学界中有关二进制的创立是否受到八卦卦象的启迪的问题,由上述的引证相信 此问题已经很清楚了。我在本书的第一编第三章第六节中已经进行了分析和说明。
1711年,尼尔教士出版了《有关中国思想的六个古典》(《Six liver classiques de I'Emp ire de la Chine》)一书。这是他研究和翻译中国古代经学思想的一部文集。1728年来华的孙璋教士,后来曾把《甲子会记》一书译成法文出版。孙璋教士本人的古代汉语水平在当时来华传教士中、在比利时籍传教士中都是一流的。他在《性理真诠》一书中用流利的古代汉语说明了他研究汉学的意义:“真道实义载于中国五经。五经者皆系古先明哲穷理尽性,躬行实践有得之妙道精理,垂之千古以教万世者也。但五经之言,至理渊邃,浅尝者不能深究其义。且秦火以后,又皆残缺失序,虽代生贤哲,遵信而接续焉,然不过收十一于千百,而五经全旨概乎不得复闻矣。”
1777年,圣彼得堡也出版了在华传教士所作的《中国哲学家的“修、齐、治、平”学说》( 《Кнатйский мудрец или наука житъ благопо лучно в обществе, состоящая в наиполе зне йщнх нравоучителъных наставленниях》)一书,
这是利用法、德、英文汉学资料编写而成的。这部解释儒家经学思想的著作,表现出了以基督教思想解说孔子学说的特点,因此,布罗夫博士在《俄罗斯的中国哲学研究》一文中认为: 儒家经典中的至理名言在本书中成了基督教式的警句,这使此书中的中国的至理名言不象出 自孔子、孟子之口,反象出自传教士的道德说教。
在18世纪的欧洲,受法国传教士们的汉学研究思想的影响,孔子并不完全是以一个哲学家 的形象被西方学术界所理解和接受的。即:“实际上,孔子并非是个哲学家。在十八世纪的 法国,他被理解成一个诚实而又博学的人。”见《Sagesse Chinoise et Philosoph ie Ehretienne: Essai sur leurs Relation Historique par Henri Bernard》一书。1930 年。换言之,吸引18世纪的西方学术界的是孔子的伦理思想,而非他的哲学。
而“诚实而又博学”是当时挑选来华传教士的首要条件之一,这实际上还是以基督教的道德 学说来看待孔子。又见1905年出版的沙畹博士(Edouard Chavannes)所作的《孔子》(《Conf ucius》)一书中对孔子的评价:“孔子学说的宗旨,实际上不是指导人们去进行理性的思考,而是让人们去行动。他的学说不是一种简单的证明,而只是一种主张。”Edouard Chavannes 《Confucius》,刊于《Revue de Paris》,1905年。因此,孔子思想在西方的传播,是以圣人和道德上的传教士二者一体化的半人半神的形象而出现的。
1861年开始,利雅格教士出版了他的研究儒家思想的系列著作《中国经典》一书。在这套以翻译为主的著作中,处处表达出了他对中国古代儒家思想的独到的研究。比如,有关宋明理学,他使用了“皇权性儒学”(“Imperial Confucianism”)的概念来进行解说。这在当时东西方汉学界都是首创性的。这一概念至今已是国际汉学界研究宋明理学中必须使用的一般 概念。当然,无庸讳言的是:这套多卷本著作的出版得到了在华英国大鸦片商人臭名昭著的 巅地的资助。
西方传教士们对古代中国哲学思想的研究,在受容期阶段的研究是以儒家传统思想和基督教 教义的一致性为中心的,而到了展开阶段以后,更多地是以对儒家传统价值观中的道德学说 的研究为核心的。

版权声明:CosMeDna所有作品(图文、音视频)均由用户自行上传分享,仅供网友学习交流。若您的权利被侵害,请联系删除!
本文链接://www.cosmedna.com/article/84414936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