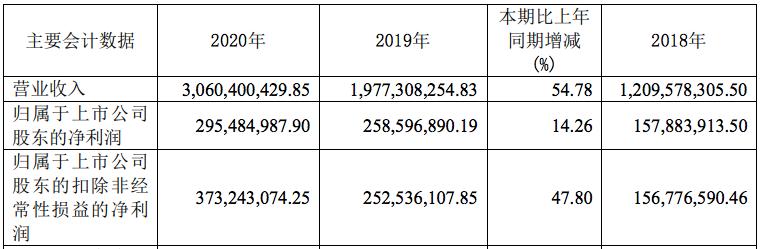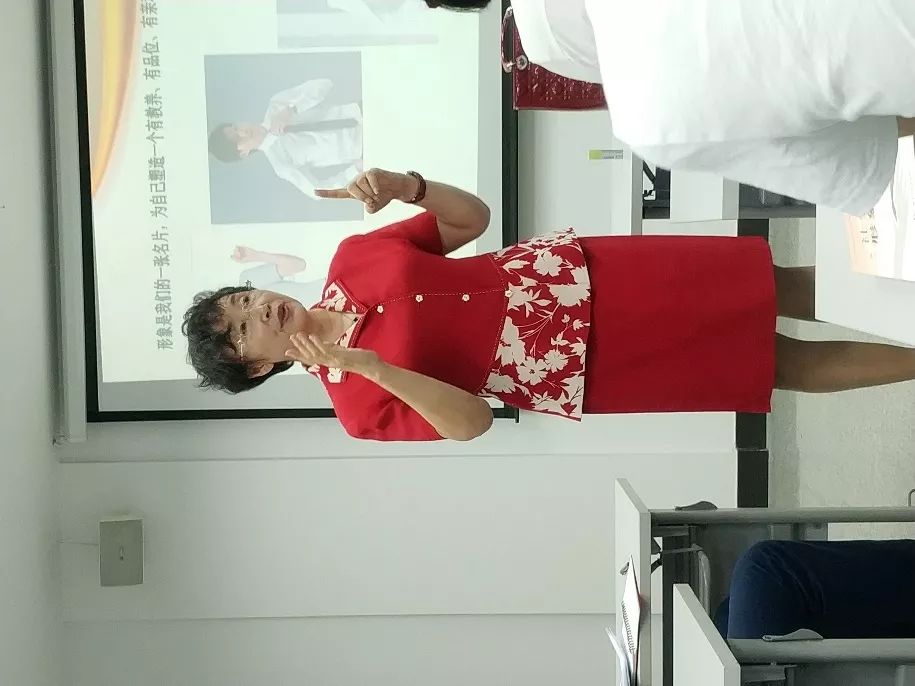展览:天下龙泉——龙泉青瓷与全球化
展期: 2019年7月16日至10月20日
地点:故宫博物院斋宫、景仁宫展厅
“天下龙泉”这个题目很容易让人想到屠龙刀和倚天剑的武林传说,放到陶瓷界改编一下应该是:陶瓷至尊,景德青花,器走天下,莫不相仿。龙泉不出,谁与争锋?青花瓷一度称霸世界,无人不晓,不过在其之前,尚有归隐林泉的前辈龙泉青瓷。“天下青花”“笔锋浓转淡”的故事,海内外争相传颂,无须赘论;“天下龙泉”的传说低调已久,却可听此次尽揽龙泉青瓷精品的故宫博物院娓娓道来。

元代龙泉青釉葫芦瓶

南宋龙泉青瓷斗笠碗

明代龙泉窑刻花折沿盘

龙泉窑青釉刻“沙阿·阿巴斯”铭凤尾尊

伊朗仿龙泉青绿釉刻划花草纹菱花口折沿盘

摄影/丁雨
由宋至明——龙泉青瓷的“三高”时代
青瓷为中国瓷器生产之始。从夏商之际的原始青瓷开始,其独霸中国陶瓷界长达三千年。其间,虽从北朝末期开始有白瓷崛起,但其直至15世纪前后尚未能撼动青瓷的地位。一般陶瓷史中对唐代“南青北白”格局的表述,来源于陆羽在《茶经》之中对越窑瓷器和邢窑瓷器的品评。且不说在陆羽的评判体系里,类银似雪的白瓷比如冰似玉的青瓷尚有不及,单是他挑拣出的六大窑场,五个都是烧青瓷的窑场,这数量便说明当时青、白两类瓷器的规模和影响。至于宋元,虽然瓷业已经百花齐放,但五大顶级名窑中有四个是青瓷窑场,这足以反映青瓷的领军地位。三千年来强势地位的取得,在于青瓷生产的不断进步,而长期的历史积淀自然令人期待更好的产品。攀登青瓷生产顶峰、完成青瓷最后辉煌的使命,最终落在了龙泉青瓷身上。
龙泉青瓷的生产始于北宋。不过北宋时的龙泉窑不过是跟在青瓷“大爷”越窑背后咿呀学步的孩童。称呼北宋越窑为“大爷”,是因为青瓷生产里以它成名最早、名声最盛、一度质量最高,可到了北宋,虽然余威尚在,但从现在的考古成果来看,多少还是露出了衰相。即便如此,其地区性影响尚存,浙江地区还是有一众窑场以模仿越窑为己任。龙泉窑便是其中之一,那时的龙泉窑青瓷喜好的是“淡妆”——透亮的釉色看起来是为了“水灵”,瓷胎上面装点的小心思还是要展现得清清楚楚。
两宋之际政局大变,也引发了河南、浙江两地瓷业格局的变化。在这变化之中,龙泉窑青瓷走上了自己的第一个高峰——生产品质的最高峰。这一高峰的出现与变局之中各方瓷业技术的碰撞关系密切。宋高宗赵构仓皇之时,并未携带太庙之中的笨重礼器。可“国之大事,惟祀与戎”,就算是逃到了南方,国家每年该有的礼仪活动仍要进行。仓促成立的小朝廷无力征集制礼器必备的铜料,便只好在礼书中找到替代的办法——以“陶木器”代之。于是,制备陶瓷礼器变成了迫在眉睫的大事。让谁来制造陶瓷礼器呢?北有汝州逃难之工,南有越州破落之窑。北宋贡窑汝窑的工匠与浙江本地原有的制瓷传统一经结合,便孕育出新的南宋官窑来。南宋官窑一时成为众多窑场追仿的对象。技术传统的碰撞与结合产生了官方计划之内的仿古陶瓷礼器,也成就了意料之外的青瓷高峰。
在变动与融合的背景之下,龙泉窑窑工开始了青瓷生产质量的腾飞。在生产技术和器型层面,均有迹象表明它与南宋官窑的交流,但其生产出的产品却有独特风格,卓尔不群。南宋时代的龙泉窑青瓷素以薄胎厚釉者最为突出,釉质略带乳浊,其釉色,或称梅子青、或称粉青、或称豆青,各具质感。前人有诗咏秘色瓷曰,“功剜明月染春水,轻旋薄冰盛绿云”,实至于南宋龙泉青瓷,方见极致真切。与后来元明者相比,其整体器型偏小,却更见雅致。在以单纯釉色为主导的宋代审美之下,龙泉青瓷碧水般的釉质感独树一帜。正因其釉色之美不可方物,因此南宋宫廷虽以官窑器物奉天地祖先,却以龙泉窑青瓷侍奉自己在宫廷中的日常生活。目前所见的南宋宫廷遗址中,以龙泉窑青瓷出土数量最多,足见皇室对龙泉青瓷的肯定。而从多年来考古所见的历代龙泉青瓷产品情况来看,学界一般公认,南宋时期的龙泉青瓷堪称其生产质量水平的最高峰。有鉴于龙泉青瓷在整个青瓷史中的地位,称南宋龙泉青瓷为中国青瓷生产质量的最高峰,亦不无道理——如冰似玉极致效果产品大量生产的实现,不负当初越窑秘色瓷所树立的标杆和汝窑、官窑的铺垫。
巅峰时代的产品,自然引来市场追捧,市场的需求自然能带动生产。只不过这一系列连锁效应的发生需要时间。正因如此,在南宋的质量高峰之后,在元代,龙泉窑青瓷迎来了自己的第二个高峰——生产规模的最高峰。平心而论,至元代中期,龙泉窑青瓷的品质略显下滑,相比于亦真亦幻、冰玉莫辨的南宋龙泉青瓷,元代的龙泉青瓷虽然不乏佳作,但多数稍显呆板。这一情况的出现,与龙泉窑青瓷迎合愈加扩大的市场或亦有关系。其重要市场中东地区对大型器物的需求,刺激了元代龙泉窑对大型瓷器的生产。生产体量较大的瓷器原本技术难度便高于普通产品,而体量的变化本身对原有瓷器效果亦有削弱。或许是对产品、市场的适应和对利润的追逐,此时龙泉窑青瓷的胎釉相较于南宋时期发生了一些变化,釉层薄厚不一,略显繁杂。此时的龙泉,窑场激增,遍野山林,窑火相应,为一时之盛。
当民间影响发展到一定程度,便会有可能上达天听。龙泉窑虽早在宋代便进入宫廷,但其明确被定为官窑为皇室供奉瓷器,却是在明代。正因其与宫廷前所未有的密切关联,学界一般认为,龙泉窑在明代初年登上自己的第三座高峰——生产地位的最高峰。文献中明确记录,从明太祖洪武年间开始,龙泉窑便承担为宫廷烧造瓷器的任务。相较于元代,明代龙泉窑风格又有变化,釉色相较之前略觉黯淡,器型整体更显敦厚。至于这样的瓷器质量的高低,只有使用者自己才有感觉吧。站在后人的角度,从龙泉窑的历史来看,老朱家虽然把龙泉窑抬上了高位,但看起来确实不如老赵家的运气好。
从宋至明,龙泉窑自身“三高”的更迭,体现的是它时间轴线上的诸多变化。龙泉窑展,取名敢与“天下”并列,当然不只因为其在纵向线索中的高峰迭起,亦因其横向空间中的空前影响。
天下归心——一直被模仿
在国际上,龙泉青瓷的名气似乎不如青花瓷响亮,这主要是因为,龙泉青瓷纵横天下的年代,如今执世界史牛耳的欧洲人在世界舞台上还只是个穷酸的配角。中东坐地起价,南非好望角的风暴实在是有点猛烈,抓耳挠腮却连瓷片的边儿都摸不着。因此,长久以来,他们对龙泉青瓷的认识远不及后起之秀青花瓷深刻。而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在达·伽马绕过好望角之前,龙泉青瓷在亚非海域的陶瓷贸易中堪称独步天下、首屈一指。
中国陶瓷的外销在9-10世纪(即晚唐五代时期)曾达到高潮,当时的贸易范围已经遍及西太平洋及印度洋沿岸。那时,浙江的越窑青瓷虽一度在湖南长沙窑、广东青瓷、北方白瓷的竞争中略占优势,但从总体来看,大体是平分秋色的格局。此后,中国瓷器的外销一度略显沉寂,直至12世纪后半叶方才又有起色。当时偏安一隅的南宋迫于经济压力,鼓励海外贸易。龙泉青瓷利用其品质及窑址区位优势,一跃而起,让曾经的陶瓷贸易市场焕发了新的活力。
至于元代,伴随着蒙元帝国的政治、军事、商业扩张,龙泉窑影响空前。从考古发现来看,其不仅几乎出土于全国各个省份,更是在海外贸易中称霸一时。龙泉系青瓷不仅重新覆盖了从朝鲜半岛、日本,到东南亚、中东、东非的市场,其在中国瓷器市场中的份额也独占鳌头,堪称前无古人。如此广大的市场,内部亦有细分。龙泉青瓷如此优雅,自然并非人人皆能消费。远端市场如东非、中东等地和消费能力更强的市场中,更流行浙江龙泉青瓷正品,如伊朗国立博物馆便藏有当年输入的龙泉青瓷多件;近端市场如东南亚、东亚等地和低端市场,则更流行购买各地仿烧的山寨龙泉青瓷。龙泉窑青瓷的仿烧,是耐人寻味的信号。它意味着,龙泉窑的商品,不仅仅征服了沿岸市场的餐桌,浸染了消费者的生活,更意味着代表着中国传统君子玉色的龙泉青瓷走进了异文化群体的心。
近水楼台先得月,龙泉窑的仿烧,从国内的福建青瓷窑场开始。如果将福建青瓷与正品龙泉放在一起,“真伪”一目了然。但从福建青瓷的广泛分布来看,其影响力却丝毫不输。特别是在东南亚等地,福建青瓷极其流行,市场份额甚至超过正品——这想必让当年的龙泉青瓷的经销商懊恼。不过,看到市场商机的何止福建窑工?东南亚、东亚诸多窑场对龙泉青瓷均有不同程度的模仿和借鉴。不过太平洋沿岸各地,传统上是中国瓷业的辐射地区,仿制中国陶瓷似早有传统。真正令人惊讶的是波斯-伊斯兰陶瓷系统对龙泉青瓷的仿效。波斯-伊斯兰陶瓷系统为与东亚陶瓷并行发展的陶瓷体系,其本有自身的发展传统,产品往往“花枝招展”,其特色与东亚者迥异。但龙泉一出,伊斯兰釉陶也不禁被“带跑了调”,硬生生开始亦步亦趋龙泉青瓷的含蓄之美,非要赶上这股青瓷大潮不可。从伊斯兰釉陶的仿制品来看,中东巧匠确实是下了一番功夫,颜色形态颇多接近之处,只是釉上光泽,难以追及。不过这“费尽心机”的努力,却让我们看到了龙泉青瓷所曾受到过的衷心青睐。
倚天剑、屠龙刀的传言,说的不只是表面的锋利,更在其中隐藏的秘笈兵法。龙泉瓷与青花瓷的故事,说的也不只是小小瓷片的漂流,背后更有人群在商品、技术、审美层面的交流与交换,更有政治、军事、经济势力的合作与角力。西方人到来之前龙泉青瓷在印度洋与西太平洋上的汪洋恣肆,不仅讲述着被中国史忽视的商业骄傲与海洋开拓,也隐喻着如今我们观看世界史的另一种视角。(丁雨)
版权声明:CosMeDna所有作品(图文、音视频)均由用户自行上传分享,仅供网友学习交流。若您的权利被侵害,请联系删除!
本文链接://www.cosmedna.com/article/75633358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