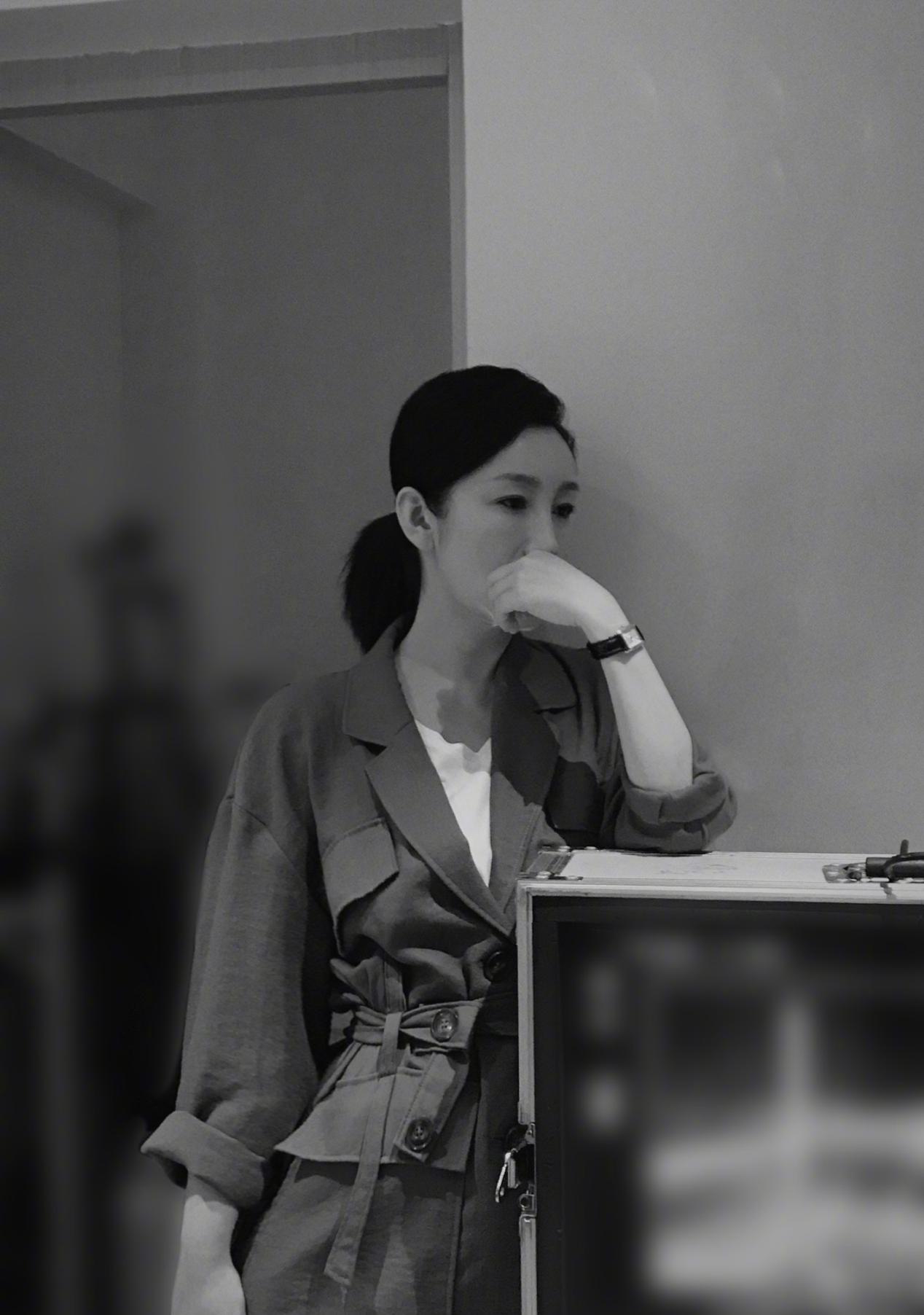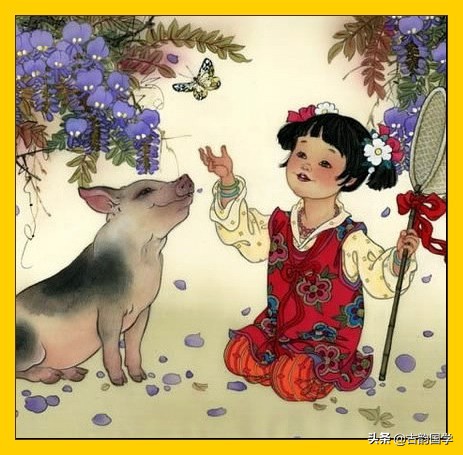《晋书》称曹叡“因母得罪”,学者卢弼亦戏言“袁胤曹嗣”,即隐喻曹叡并非曹氏血脉。“袁胤”之说固属妄语,无足采信;但甄后赐死与曹叡失宠却真实存在,而这一事件又对三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及至(魏)明帝,因母得罪,废为平原侯。--《晋书 阎缵传》
从某种意义上看,明帝“沉毅断识,任心而行”的性格特征,很大程度上源自其少时的悲惨经历。
生母赐死令其压抑心性,谦退自守;而独擅权柄之后,又带来报复般的肆意妄为。明帝统治期间“宫馆是营”、“录夺士女”,大兴土木,荒淫自恣,可谓长期压抑之后的病态行径。而这一切病态行径的根源,又皆在甄后之诛。
自(明帝)在东宫,不交朝臣,不问政事,唯潜思书籍而已。--王沈《魏书》
鉴于甄后之死属于魏朝之“国恶”,因此王沈《魏书》、陈寿《魏志》对此皆语焉不详,百般回护。然而通过对《典论》、《魏略》、《种瓜篇》的线索分析,可知其赐死始末相当复杂,远非一句单纯的“愈失意,有怨言”所能概括。
本文想就现存史料,探讨甄后赐死始末,并论述其对曹叡性格的负面影响。
本文共 11000 字,阅读需 22 分钟
“袁胤曹嗣”及其反映的血统问题
“袁胤曹嗣”之说,波流已久。其根源在于《明帝纪》对曹叡年龄的混乱描述。
明帝之崩,时年卅六,袁胤曹嗣,深滋疑实,杀母留子,藉以灭口。--《三国志集解》
陈寿称曹叡崩于魏景初三年(239),卒年“三十六”。按此,曹叡当生于东汉建安九年(204)。
三年春正月丁亥……帝崩于嘉福殿,时年三十六。--《魏书 明帝纪》
然而曹丕纳甄氏,事在建安九年(204)八月。若如此,则曹丕、甄氏自成婚至生子,前后竟不足四个月,令人疑窦丛生。
及冀州平,文帝纳(甄)后于邺。--《魏书 文昭皇后传》
(九年)八月,审配兄子(审)荣夜开所守城东门内兵。配逆战,败,生禽配,斩之,邺定。--《魏书 武帝纪》
后世学者遂据此发微,质疑明帝血统,甚至根据甄氏的过往婚史,逆推曹叡乃袁熙之遗腹子,此即“袁胤”之所由来。
窃谓承祚(指陈寿)此文,实为曲笔,读史者逆推年月,证以甄夫人之赐死,魏明之久不得立为嗣,则元仲(指曹叡)究为谁氏之子,可不言而喻矣!--卢弼《三国志集解》
然而考之诸书,根据袁熙的活动路径与曹军的攻邺时间,可知“袁胤”之说断不可信。
按《魏书》与《后汉书》,袁熙自建安四年(199)“出为幽州(刺史)”后便未见返邺记载,而甄氏则“留(邺县)养姑(侍奉婆婆)”,直至被曹丕所纳。
建安中,袁绍为中子熙纳之。(袁)熙出为幽州,(甄)后留(邺县)养姑。--《魏书 文昭皇后传》
(袁绍)又以中子(袁)熙为幽州,甥高干为并州……简精卒十万,骑万匹,将攻许。--《魏书 袁绍传》

注:按《后汉书 献帝纪》,公孙瓒败殁于四年三月,袁熙“为幽州”当在此后;按《魏书 武帝纪》,曹操于四年八月“进军黎阳”,同年九月“分兵官渡”,可知袁绍南下亦在此时,结合《绍传》,可知袁熙“为幽州”当在此前。因此,袁熙出镇幽州,当在建安四年(199)三月至八月间。
建安九年(204)五月至八月,曹军攻邺县,袁尚“还救城”,结果被曹操“逆击破之”,被迫遁走中山;复战再败,遂赴故安投奔次兄袁熙。
自五月至八月,(邺)城中饿死者过半。(袁)尚闻邺急,将军万余人还救城,操逆击破之……众大溃,尚奔中山……(曹操)攻尚于中山。尚败,走故安从(袁)熙。--《后汉书 袁绍传》
故安县属涿郡,即今河北固安,可知袁熙自出为幽州刺史(199)便长驻当地,直至建安九年(204)。袁熙、甄氏既数年不得相见,可知“袁胤曹嗣”之说实属妄言。
(涿郡)故安,易水出,雹水出。--《续汉书 郡国志》
另按邺县城破时间(建安九年八月)而论,若曹叡果生于建安九年(204),则甄氏与曹丕成婚之初便至少有六个月之身孕,岂能瞒过众人耳目?曹操、曹丕又焉能不知?曹氏父子虽于男女关系方面颇为通达,又岂会传位袁氏血脉,自绝宗祀,坐笑天下?
因此,不仅曹叡的血统与袁熙毫不相涉,就连曹叡的生卒年记载都存在严重问题。
览查史料,包括裴松之(南朝)、周婴(明代)、侯康(清代)在内的诸多学者,虽对明帝年龄多有探究,却均未达其旨。现代学者王雪晶在《曹叡研究》中对此辨析甚明,兹不赘引。
其实曹叡年龄的真正线索,恰恰隐藏在《文帝纪》与《明帝纪》中。
按《文帝纪》,曹叡在延康元年(220)五月受封“武德侯”;按《明帝纪》,曹叡受封“武德侯”时,年方“十五”。
(延康元年)五月戊寅,天子命王追尊皇祖太尉(曹嵩)曰太王,夫人丁氏曰太王后,封王子(曹)叡为武德侯。--《魏书 文帝纪》
(曹叡)年十五,封武德侯。--《魏书 明帝纪》
显而易见,延康元年(220)曹叡年十五,则其生年当在建安十一年(206)。可知曹丕于九年(204)八月纳甄氏,甄氏于翌年(205)有孕,复一年(206),遂生曹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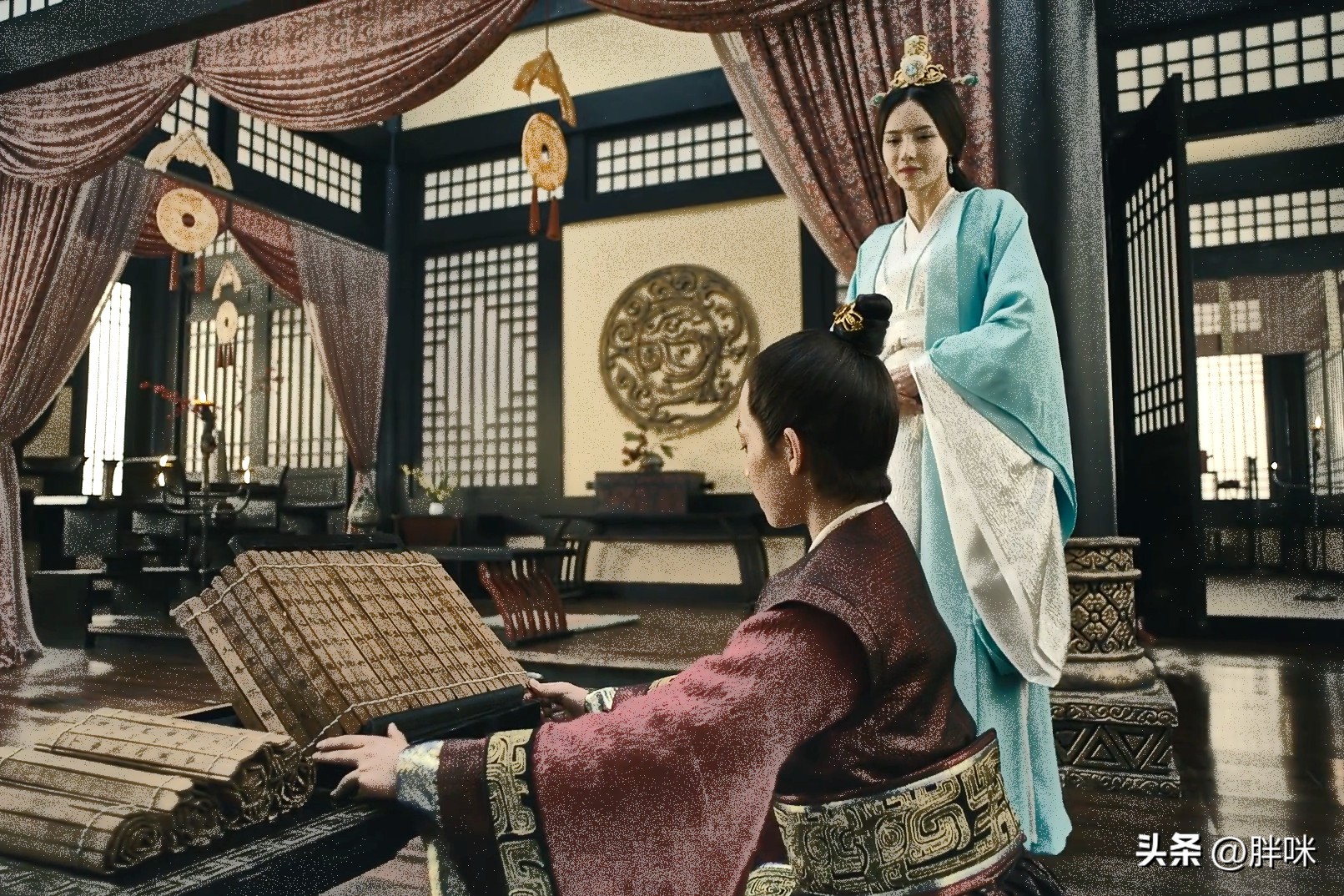
如此,则曹叡之血脉问题便得到完美且合理之解释,绝无疑点。近代学者陆侃如在《中古文学系年》中亦勘定曹叡生于建安十一年(206),诚是。
唯一的问题,便是明帝若生于建安十一年(206),按其崩于景初三年(239),其卒年当为三十四,不得为三十六也。
对此问题,学者王雪晶亦提出开拓性意见。即曹叡因“景初改历”而虚增一岁,卒年并非三十四岁,实为三十三岁。
王氏认为,晋代之后行草盛行,“三”与“六”之字形亦相类,史家誊录或有讹误,致使“三十三”被误作“三十六”。及至南朝,裴松之遂难辨真伪,因生疑窦。
三字首笔为一横……若抄录者偏向于行草,那么最后的收笔一横,看上去类似起伏不定的两点,亦属常事。晋朝之时,活版印刷还未发明,文献皆以笔录为主,只要开始时一人写错,那么后来者便会继续错下去。--王雪晶《曹叡研究》
至于上文提到的“景初改历”,即曹叡在其统治中后期修改历法,改“青龙五年春三月”为“景初元年夏四月”,凭空虚增了一月。而曹叡又恰好崩于景初三年(239)春正月,若按旧历计算,则曹叡当崩于景初二年(238)冬十二月。
魏得地统,宜以建丑之月为正。三月,定历改年为孟夏四月。--《魏书 明帝纪》
(明)帝从其议,改青龙五年春三月为景初元年孟夏四月,服色尚黄,牺牲用白,从地正也。--《魏书 高堂隆传》
如此,若按太和历(旧历)计算,其实为三十三岁;若按景初历(新历)计算,亦不过三十四岁。裴松之称其“计至此年正月,整三十四年耳”,即如此类。
鉴于《文帝纪》与《明帝纪》对曹叡“封武德侯”的时间记载甚明,且能互文印证,因此曹叡之生卒年份与血脉归属,断无可质疑之处。至于《魏志》所载“年三十六”者,当为晋世之后的传抄讹误,今人(陆侃如、王雪晶)辨析甚明,可堪参详。
袁氏家妇的妒忌、干政之风
甄氏之死的主要原因,在于其习自前夫家族的妒忌、干政风气。
袁绍家族的女眷以“乱政”、“善妒”闻名,绍妻刘氏不仅“追妒亡魂,戮及死人”,还一力唆使袁谭、袁尚兄弟相残,致使宗族湮灭。曹丕耳闻目见,对此深恶痛绝。
刘氏性酷妒,绍死,僵尸未殡,宠妾五人,刘尽杀之。--《典论》
绍听顺妻(刘氏)意,欲以尚为嗣,又不时决定。身死而二子(袁谭、袁尚)争国,举宗涂地,社稷为墟。--《典论》
在曹丕撰写的《典论 内诫》中,他不遗余力地痛斥妇人妒忌、乱政之祸,甚至得出结论:“袁绍虽蔽,亦由恶妇。”可见曹丕对袁家女眷成见甚深,乃至视之为“恶妇”。甄氏无疑亦在其中,只不过彼时的她因色而宠,深受曹丕迷恋,因此暂时掩盖了双方矛盾。
追妒亡魂,戮及死人,恶妇之为,一至是哉……绍虽蔽乎?亦由恶妇!--《典论》
文帝纳后于邺,有宠,生明帝及东乡公主。--《魏书 文昭皇后传》

一如袁氏诸妇,甄氏亦有“专擅”之行。虽然王沈《魏书》盛赞甄氏心胸宽广,且列举诸多史料以增色添彩,但裴松之早已注意到其中的矛盾记载,遂做出结论:“卞、甄诸后言行之善,皆难以实论。”
魏史若以(赐死甄氏)为大恶邪,则宜隐而不言,若谓为小恶邪,则不应假为之辞,而崇饰虚文(指王沈在《魏书》中杜撰的材料)乃至于是,异乎所闻于旧史。推此而言,其称卞、甄诸后言行之善,皆难以实论。--裴松之
最典型的例证,便是甄氏与曹丕成婚之初便把持后宫,专擅专宠,与《魏书》塑造的温婉形象判若两人。刘孝引《魏略》补注《世说新语》亦提到甄后“擅室数岁”。按曹叡与诸弟的年龄差异而论,此言当为不虚。
至魏黄初元年(220),年近四旬的甄氏已年老色衰,“色衰”即意味着“爱驰”,也意味着“恩绝”。因此她虽替曹丕诞育长子(曹叡)、长女(东乡公主),却久不得立为皇后,甚至遭遇冷落,被留置邺县,不得与曹丕相见。
夫以色事人者,色衰而爱驰,爱驰则恩绝。--《汉书 李夫人传》
文帝即王位,六月,(曹丕)南征(即赴洛阳继位),(甄)后留邺。--《魏书 文昭皇后传》
至此,甄氏身为“袁氏内妇”的另一重隐藏性格随即发作,即干乱政务。
《文昭皇后传》对甄氏的死因记载十分模糊,仅云其“愈失意,有怨言”,实际按照“文帝践阼”的历史背景,以及曹叡“以其母诛,故未建为嗣”的处理结果来看,甄氏彼时的“怨言”,无疑是针对魏朝国本,意在谋取皇后与储君之位。
(文帝)践阼之后,山阳公奉二女以嫔于魏,郭后、李、阴贵人并爱幸,(甄)后愈失意,有怨言。帝大怒。--《魏书 文昭皇后传》
从时代背景出发,曹丕既然已经“践祚”,那么理所当然要立皇后、立太子。按甄氏的想法,论年资高低、论子嗣长幼,她都应该荣登后位,至于其子曹叡则是储君的不二之选。
而曹丕最恨妇人干政,他在黄初三年(222)九月,即赐死甄氏之翌年,便下诏怒斥“夫妇人与政,乱之本也”,甚至立下祖训:“后族之家不得当辅政之任,又不得横受茅土之爵”,若有违背者,“天下共诛之”。言辞可谓凶厉。
九月甲午,诏曰:“夫妇人与政,乱之本也。自今以后,群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当辅政之任,又不得横受茅土之爵;以此诏传后世,若有背违,天下共诛之。”--《魏书 文帝纪》
从时间背景上看,曹丕此言虽是针对其母卞太后(卞氏彼时回护曹植,令曹丕难堪),但也未尝不是对甄氏故迹的迁怒。
时(文)帝欲治弟(曹)植之罪,偪于太后,但加贬爵。--《魏书 周宣传》
正缘于此,甄氏赐死之后,曹叡旋即失宠,从“生而太祖爱之,常令在左右”的尊贵待遇,一夜跌落到“以其母诛,故未建为嗣”的凄凉境地,甚至被迫低调行事,不与朝臣往来,直至曹丕“病笃”,才被“立为皇太子”。
(明)帝与朝士素不接。--《魏晋世语》
(曹叡)以其母诛,故未建为嗣。七年夏五月,(文)帝病笃,乃立为皇太子。--《魏书 明帝纪》

毫无疑问,甄氏的妒忌、干政之风,既害了身家性命,也险些连累爱子。众所周知,历朝之废储,鲜有善果。
从某种意义上看,曹叡能够跌跌撞撞地登基,也得益于曹丕的短寿。但即使在曹丕短寿的情况下,曹叡的地位也并不稳固,因为曹丕曾一度考虑过立庶子曹礼为嗣,其处境凶险如此。
文帝始以(明)帝不悦,有意欲以他姬子京兆王(曹礼)为嗣,故久不拜太子。--《魏略》
甄氏与曹植的暧昧关系
甄氏之死的另一原因,即源自她与曹植的暧昧关系。
关于甄氏与曹植的风流艳史,虽多为小说家之妄言,但也存在些许线索,曹植所撰《感甄赋》即为其一。
曹植在《赋》中一方面盛赞洛神之绝色,另一方面又感叹人神道殊、不能结合。此赋的成文时间恰在甄氏之死翌年(222),不由令人遐思联翩。
黄初三年,余朝京师,还济洛川。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曰宓妃。感宋玉对楚王神女之事,遂作斯赋。--《感甄赋》
明帝对叔父与生母的关系或有耳闻,他登基之后,遂改《感甄赋》为《洛神赋》,似为遮掩。
魏东阿王(曹植),汉末求甄逸女,不遂,后作《感甄赋》,明帝改为《洛神赋》。--《文选 洛神赋》李善注引《记》
鉴于甄氏是文帝之妇,明帝之母,其形象问题涉及皇室尊严,因此无论她是否与曹植有染,皆不可能被录于史书。更何况曹植死后,曹叡便明令秘府机构彻底销毁与曹植相关的一切罪状记载,因此对曹植、甄氏的关系问题,也便更加无迹可寻。
其收黄初中诸奏(曹)植罪状,公卿已下议尚书、秘书、中书三府、大鸿胪者皆削除之。--《魏书 陈思王传》
不过天网恢恢、疏而不漏,除《感甄赋》外,王沈《魏书》中还存在一处显著线索,暗示了曹植与甄氏的暧昧关系。
建安二十一年(216),曹操东征孙权,“武宣皇后、文帝、明帝及东乡公主皆从”,而甄氏则留居邺县。结果翌年(217)大军班师之后,众人竟见到独居已久的甄氏“颜色丰盈”,纷纷表示惊诧;甄氏对此则随意搪塞,称“(曹叡)等自随(卞)夫人,我当何忧”。
二十一年,太祖东征,武宣皇后、文帝及明帝、东乡公主皆从,时(甄)后以病留邺。二十二年九月,大军还,武宣皇后左右侍御见后颜色丰盈,怪问之曰:“(甄)后与二子(曹叡、东乡公主)别久,下流之情,不可为念,而(甄)后颜色更盛,何也?”--王沈《魏书》

按常理而论,公公(曹操)、婆婆(卞氏)、丈夫(曹丕)、儿子(曹叡)、女儿(东乡公主)皆随军出征,身为妻子的甄氏独守空闺,理应辗转反侧,思量亲人,但她却“颜色丰盈”、甚至“颜色更盛”,不由令人狐疑满腹。
实际虽然彼时曹氏亲眷皆随军出征,但其中却有一人却被留置邺县。此人便是曹植。
按《陈思王传》,曹植在建安十九年(214)受封临淄侯,随后在“太祖征孙权”时“留守邺”。
十九年,徙封(曹植)临菑侯。太祖征孙权,使植留守邺。--《魏书 陈思王传》
显而易见,建安二十一年(216)诸曹东征时,身为小叔子的曹植与嫂子甄氏,共处邺县,且前后历时至少半载(216-217)。虽然王沈出于避讳需要,对此未敢进一步明言,但单凭这句“颜色丰盈”便胜过千言万语。众所周知,无论男女,只有在身心愉悦时才会“颜色丰盈”,其中硍节,无需赘言。
注:按《武帝纪》,曹操于二十一年冬十月征孙权,二十二年春三月旋军。
唐人李商隐在《无题》诗中亦曾戏说魏晋时代的宫闱秘闻,诗云:“贾氏窥帘韩掾少,宓妃留枕魏王才。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
飒飒东风细雨来,芙蓉塘外有轻雷。金蟾啮锁烧香入,玉虎牵丝汲井回。贾氏窥帘韩掾少,宓妃(指甄氏)留枕魏王才(指曹植)。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无题 飒飒东风细雨来》
诗文前半句指贾充之女与韩寿私通之事;后半句则指曹植与甄氏的宫闱秘闻。可见二人的风流韵事,至晚在唐代便已人所共知,甚至被文人墨客用作吟风弄月的素材。
(贾)充僚属与(韩)寿燕处,闻其芬馥,称之于充。自是充意知女与寿通,而其门阁严峻,不知所由得入……充秘之,遂以女妻寿。--《晋书 贾充传》
曹植虽与甄氏年龄差距颇大(相差九岁),但并不影响二人存在暧昧往来。因为诸曹在婚姻、男女关系方面一贯不守礼法。
比如曹操好纳人妇,乃至蓄养假子以作炫耀;曹丕的前后两任夫人甄氏、郭氏年龄皆大于己;曹丕甚至在曹操死后临幸其父生前侍女,悖逆人伦,以致遭到时论非议。
(秦)朗随母氏畜于(曹)公宫,太祖甚爱之,每坐席,谓宾客曰:“世有人爱假子如孤者乎?”--《献帝传》
魏武帝崩,文帝悉取武帝宫人自侍……太后问:“何时来邪?”曰:“正伏魄时过。”因不复前而叹曰:“狗鼠不食汝余,死故应尔!”--《世说新语》
至于曹植,被称作“性简易”,亦即不拘礼法。他又嗜酒放肆,纵车驰于司马门,以致满朝哗然。曹植之妻崔氏甚至公然违背禁令(曹操彼时提倡节俭),盛装纹绣,遂遭赐死。曹植家风流荡如此,其本人行径可想而知。
(曹植)性简易,不治威仪……尝乘车行驰道中,开司马门出。太祖大怒,公车令坐死。--《魏书 陈思王传》
武皇帝之时,后宫食不过一肉,衣不用锦绣,茵蓐不缘饰。--《魏书 卫觊传》
(曹)植妻衣绣,太祖登台见之,以违制命,还家赐死。--《魏晋世语》

曹丕与曹植争嫡多年,可谓势同水火;因此在涉及男性尊严的风言风语传至曹丕耳中时,他会作何感想也便不言自喻。甄氏“赐死葬邺”便是对此事的最佳注脚。从埋葬地点看,曹丕甚至不愿甄氏与其合葬(曹丕葬于洛阳首阳陵),厌弃之情溢于言表。
(甄)后愈失意,有怨言。帝大怒,二年六月,遣使赐死,葬于邺。--《魏书 文昭皇后传》
(文)帝崩于嘉福殿,时年四十。六月戊寅,葬首阳陵。--《魏书 文帝纪》
在曹叡继位后,他虽在洛阳为生母立庙,但也并未将甄氏的陵寝迁出邺县,只是改葬于朝阳陵。可知即使是曹叡,出于种种考虑,也不愿将生母与生父合葬,其中因由,耐人寻味。
己未,有司奏文昭皇后立庙京都。--《魏书 明帝纪》
十二月辛未,改葬文昭甄后于朝阳陵。--《魏书 明帝纪》
曹叡的压抑境遇与病态性格
鉴于生母之过往事迹与赐死结局,身为人子的曹叡,自然遭到生父迁怒,长期处在压抑环境之中,这也塑造了他的病态人格。
(1)韬光养晦,低调求存
《明帝纪》引《魏末传》中有一处重要线索,即曹叡登基之前“与朝士素不接”,以至其登基之后“群下想闻风采”,竟不得不选取一个代表(侍中刘晔)前去与曹叡交谈,借此揣摩新君。
(曹叡)即位之后,群下想闻风采。居数日,独见侍中刘晔,语尽日。众人侧听,晔既出,问:“何如?”晔曰:“秦始皇、汉孝武之俦,才具微不及耳。”--《魏末传》
这是一个非常令人难堪的信号。因为它代表彼时的曹叡班底差,声望低,深居简出,籍籍无名;所以才需要群臣揣度试探。
通常而论,储君必定具备雄厚的幕僚班底,且幕僚人选一定是文武茂异,当世俊杰。魏之曹丕、蜀之刘禅、吴之孙登、孙和皆如此。
初,备以诸葛亮为太子太傅,及禅立,以亮为丞相,委以诸事。--《魏略》
赤乌五年,立(孙和)为太子,时年十九。阚泽为太傅,薛综为少傅,而蔡颖、张纯、封俌、严维等皆从容侍从。--《吴书 孙和传》
早在上述储君继位之前,其声望便已传遍境内,甚至远至异国。比如孙权在曹丕继位时(220)便知道对方“年已长大,承操之后”,甚至还担心自己“不及之”。
逮(曹)丕继业,年已长大,承(曹)操之后,以恩情加之,用能感义。--《吴书 诸葛瑾传》
初,魏文帝即位,(孙)权尝从容问群臣曰:“曹丕以盛年即位,恐孤不能及之,诸卿以为如何?”--《吴录》
与此相对,孙权对曹叡的看法则十分轻蔑,视其为“幼弱”之徒,可见曹叡登基前毫无声望可言。
(孙权曰)今(曹)叡幼弱,随人东西,此曹(曹真、陈群)等辈,必当因此弄巧行态,阿党比周,各助所附。--《吴书 诸葛瑾传》

从现存史料看,曹叡继位前的幕僚班子中可考者仅有郑称、张茂、毕轨、李丰、曹爽、毌丘俭、高堂隆等人。且郑称“儒生”,张茂“乡里”,皆湮灭无闻;曹爽德薄位尊,以覆其族;毕轨、李丰浮华相尚,不以道终;唯毌丘俭、高堂隆才略兼备,可谓俊逸。
注:郑称、张茂事见《明帝纪》引《魏略》;毕轨事见《曹爽传》引《魏略》,李丰事见《夏侯玄传》引《魏略》;曹爽、毌丘俭、高堂隆各有列传,文多不载。
概而论之,相比于同时代之储君,曹叡的班底可谓简陋,名望可谓黯淡。因此直至曹叡继位,满朝臣僚都对这个新君一无所知,被迫推选刘晔前往探听口风。
按曹丕在“病笃”之际才立曹叡为太子,可知曹叡登基实属意外。若非曹丕盛年暴毙,曹叡不仅没有继位机会,甚至可能遭到赐死(曹丕一度欲立曹礼为太子,见前引《魏略》),一如蜀之刘封一般。
七年夏五月,(文)帝病笃,乃立(曹叡)为皇太子。(五月)丁巳,(曹叡)即皇帝位。--《魏书 明帝纪》
在曹叡的存世诗文《种瓜篇》中,曾借“菟丝”、“萍藻”隐喻新婚女子,抒发“妇人从夫”的依恋之情,似抱憾生母之不幸命运。萍漂藻寄,浮水无根,又似隐喻其少时处境,朝不谋夕的悲戚之情跃然纸上。推此而论,他“口吃寡言”的隐疾可能也源自那一灰暗时期。
兔丝无根株,蔓延自登缘。萍藻托清流,常恐身不全。被蒙丘山惠,贱妾执拳拳。天日照知之,想君亦俱然。--《种瓜篇》
魏明帝天姿秀出,立发垂地,口吃少言,而沉毅好断。--孙盛
有鉴于此,曹叡从长期的压抑环境下骤然得到解脱,一朝黄袍加身,荣登大宝;在大悲大喜、大落大起之下,心态膨胀,性格扭曲,也便势所必至。
(2)壮志暗藏,政自己出
曹叡虽在生母遇害后长期矫情忍性,韬光养晦,但他一直“留意于法理”,这是心存壮志的典型标志。
(明帝)好学多识,特留意于法理。--王沈《魏书》
作为一个皇子,曹叡的人生轨迹无外乎登基为帝或出为藩王,总之他绝无可能供职于廷尉府,因此“留心法理”的唯一原因便是为了君临天下而做准备。按其自述:“狱者,天下之性命也。”壮志宏图足见一斑。
冬十月,改平望观曰听讼观。(明)帝常言“狱者,天下之性命也”。--《魏书 明帝纪》
曹操“好法、术”,而曹叡“生而太祖爱之,常令在左右”,无疑亦精通刑名之道。“沉毅断识”的性格特征,“一经耳目,终不遗忘”的超凡记忆,当源自少时的学术训练。
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晋书 傅玄传》
(曹叡)生而太祖爱之,常令在左右。--《魏书 明帝纪》
(明帝)性特强识,虽左右小臣官簿性行,名迹所履,及其父兄子弟,一经耳目,终不遗忘。--王沈《魏书》

有赖于此,曹叡登基未久便独揽权柄,通过一系列政治手腕,先后将四大辅政架空。他令曹真镇关中、令曹休镇淮南、令司马懿屯宛县,授以方略之任,使之远离京畿,无法干预朝政。
至于陈群,虽留居洛阳,不过上书言事,唯唯而已。明帝因此被裴松之誉为“一时明主,政自己出”。
(3)大兴土木,荒淫自恣
曹叡在军政方面颇有建树,外制吴蜀,内御群臣;但其本人的私生活却极端糜烂,用荒淫无度形容毫不为过。
曹叡因“母诛”而导致“未建为嗣”,甚至被迫伪装成无心朝政的闲散皇子,长期压抑自己的本性;因此在一朝发迹之后,他立刻开始了报复性的娱乐活动。从可见记载看,曹叡在营建宫室、采择女色方面的兴致已近乎病态,甚至危及国政。
早在“吴、蜀数动,诸将出征”的背景下,曹叡便昼夜宣淫,乐此不疲,“盛兴宫室,留意玩饰,赐与无度,帑藏空竭”;如此尤嫌不足,他“又录夺士女,简选其有姿色者内之掖庭”,近乎禽兽之举。
吴、蜀数动,诸将出征,而(明)帝盛兴宫室,留意于玩饰,赐与无度,帑藏空竭;又录夺士女前已嫁为吏民妻者,还以配士,既听以生口自赎,又简选其有姿色者内之掖庭。--《魏略》
彼时曹叡的后宫之中“自贵人以下至掖庭洒扫者,凡数千人”,荒淫程度已与后世的孙皓、司马炎相类;他还“选信者六人,以为女尚书”,公然违背祖训,令妇人染指政务。
(明)帝耽于内宠,妇官秩石拟百官之数,自贵人以下至掖庭洒扫者,凡数千人,选女子知书可付信者六人,以为女尚书,使典省外奏事,处当画可。--《资治通鉴 魏纪》
从某种意义上看,曹叡此举似在忤逆其父,以报生母被诛之恨。其父淫乱(曹丕纳曹操侍妾,见前引《世说新语》),曹叡便要更加淫乱;其父遗令“后宫不得干政”,曹叡便要设立女官,故意拆台,发泄心中怨愤。
除了贪图女色,曹叡的另一喜好便是大兴土木。《杨阜传》、《高堂隆传》对此描述甚多,兹不赘言。陈寿腹诽曹叡“宫馆是营”,亦属此类。
外人咸云宫人之用,与兴戎军国之费,所尽略齐。民不堪命,皆有怨怒。--《魏书 高堂隆传》
(明)帝愈增崇宫殿,彫饰观阁……百役繁兴,作者万数。--《魏书 高堂隆传》
(明帝)不先聿脩显祖,阐拓洪基,而遽追秦皇、汉武,宫馆是营,格之远猷,其殆疾乎!--《明帝纪》赞语
考诸史料,曹丕对营造宫室的兴趣倒是相对有限,他还比较提倡节俭、薄葬。比如他在《终制》中明令“(葬品)无施苇炭,无藏金银铜铁,一以瓦器”,“饭含无以珠玉,无施珠襦玉匣”,颇具通达之风。
无施苇炭,无藏金银铜铁,一以瓦器,合古涂车、刍灵之义。棺但漆际会三过,饭含无以珠玉,无施珠襦玉匣,诸愚俗所为也。--《终制》
相较其父,曹叡可谓奢靡铺张,若从其少时经历推断,如此行径可能亦是逆反心理作祟。即曹丕提倡节俭,那曹叡便要肆意挥霍,以示不同。
(4)追痛爱女,怠慢生父
曹丕出殡之时,曹叡并未前往送葬,虽然其托言“暑热”,但身为人子、身为帝王,如此行径亦堪称不孝。
文皇帝、武宣皇后崩,陛下皆不送葬。--《魏书 杨阜传》
明帝将送葬,曹真、陈群、王朗等以暑热固谏,乃止。--《魏氏春秋》
与此相对,在女儿曹淑病逝时,曹叡却大张旗鼓,哀恸备至,乃至“举朝素衣,朝夕哭临”。他还亲自替女儿送葬,与其对待生父的冷淡态度形成鲜明对比。
皇女(曹)淑薨……(曹叡)以成人礼送之,加为制服,举朝素衣,朝夕哭临,自古已来,未有此比。--《魏书 陈群传》

需要特别注意,曹淑属于早夭,她死时尚“未期月”,实际是出生未久即告夭折。因此曹叡对这个尚未满月的女儿究竟能有多深的感情,实在很成问题。
八岁下殇,礼所不备,况(曹淑)未期月。--《魏书 陈群传》
然而曹淑还有另一重身份,即甄夫人已故侄孙甄黄之妻,按《文昭皇后传》,可知这桩“婚事”乃是由曹叡主持。因此,与其说曹叡是追痛曹淑,莫不如他是追痛母族(甄氏)之妻儿亲眷。
太和六年,明帝爱女(曹)淑薨,追封谥淑为平原懿公主,为之立庙。取(甄)后亡从孙(甄)黄与合葬,追封黄列侯。--《魏书 文昭皇后传》
在曹丕与曹淑的丧葬待遇上,曹叡的极端态度可谓刺眼。从种种记载看,他对生母的追痛依恋,与对生父的怨恨憎恶,已近乎扭曲刻意。
(5)压制宗亲,迫害曹植
曹叡执政的另一特点,便是压制宗亲,以至“诸侯王法禁急切,吏察之急,至于姻亲皆不敢相通问”。
黄初以来(指黄初至太和年间),诸侯王法禁严切。吏察之急,至于亲姻皆不敢相通问。--《资治通鉴 魏纪》
一般观点,往往将曹叡此举视作对曹丕既定政策的延续,但实际这一逻辑存在问题。曹丕压制宗亲,是因为他本人深受夺嫡之困,不得不如此;曹叡无此困扰,又有何必要沿袭曹丕之故迹?
如若仔细观察曹叡的监视对象,便会发现曹叡压制宗亲,主要是针对曹植。
彼时“藩国既自峻迫,寮属皆贾竖下才,兵人给其残老,大数不过二百人”,如此待遇已经堪称峻急,而“(曹)植以前过,事事复减半”。显而易见,在诸多受到迫害的藩王中,曹植的受害程度最深。
藩国既自峻迫,寮属皆贾竖下才,兵人给其残老,大数不过二百人。又(曹)植以前过,事事复减半,十一年中而三徙都,常汲汲无欢。--《魏书 陈思王传》
《陈思王传》中辑录了大量曹植对曹叡的上书,疏文多次提到“禁锢明时”、“兄弟乖绝”,言辞可谓悲戚;曹叡虽然“优文答报”,但也并未因此放松对曹植的监视。
至于臣者,人道绝绪,禁锢明时,臣窃自伤也……近且婚媾不通,兄弟乖绝,吉凶之问塞,庆吊之礼废,恩纪之违,甚于路人,隔阂之异,殊于胡越。--《魏书 陈思王传》
按《陈思王传》,自曹叡继位伊始,曹植这个骨肉至亲的皇叔便无缘瞻仰圣颜,而他也在日复一日的上书中蹉跎岁月,直至太和六年(232)郁郁而终。
(曹)植每欲求别见(曹叡)独谈,论及时政,幸冀试用,终不能得。既还,怅然绝望……十一年中而三徙都,常汲汲无欢,遂发疾薨,时年四十一。--《魏书 陈思王传》

不难看出,曹叡根本就不想见这个叔父。其实曹植与曹丕虽为政敌,但与曹叡并无矛盾,究其根源,无外乎曹植与甄氏昔日曾有过一段隐晦的暧昧关系(见前文),令身为天子的曹叡羞愤且难堪,因此对曹植刻意回避,甚至屡加迫害。
直至曹植逝世,曹叡仍不忘处理与叔父有关的线索,他诏令尚书、秘书、中书三府与鸿胪寺,将与曹植相关的案卷材料全部销毁,将一切可能影响到明帝母子形象的蛛丝马迹,从历史中彻底抹去。
其收黄初中诸奏(曹)植罪状,公卿已下议尚书、秘书、中书三府、大鸿胪者皆削除之。撰录(曹)植前后所著赋颂诗铭杂论凡百馀篇,副藏内外。--《魏书 陈思王传》
小结
曹丕见异思迁,寡恩薄幸,为夫不义,为父不仁;甄氏专擅善妒,祸及爱子,为妻不贤,为母不慧;曹叡任心而行,昧于礼法,为君失道,为子不孝。
一言蔽之,文、明二帝,论功绩可为中才之主,论亲情则是人间悲剧。而在这桩悲剧的漩涡中央,则是甄氏之亡魂。无情最是帝王家,此言诚是。
也正是这一桩桩人间悲剧,塑造出一张张病态面孔,它令“仁冠群子、名昭海内”的多情之人沦为残害发妻、“以糠塞口”的无情之辈;它令“天姿秀出”、“好学多识”的风华少年变作“宫馆是营”、“录夺士女”的荒淫之徒;它也令“翩若惊鸿,婉若游龙”的绝代佳人化作一抔黄砂残土,随风消逝,将最初的美好恬淡扭曲为最终的恐怖模样。
甄后之诛,由郭后之宠,及殡,令被发覆面,以糠塞口。--《汉晋春秋》
昔者,(明)帝从文帝猎,见子母鹿。文帝杀鹿母,使帝射鹿子,帝不从,曰:“陛下已杀其母,臣不忍复杀其子。”每读于此,皆抚卷叹息。
我是胖咪,头条号历史原创作者。漫谈历史趣闻,专注三国史。从史海沉钩中的蛛丝马迹、吉光片羽,来剖析展开背后隐藏的深意。
Thanks for reading.
版权声明:CosMeDna所有作品(图文、音视频)均由用户自行上传分享,仅供网友学习交流。若您的权利被侵害,请联系删除!
本文链接://www.cosmedna.com/article/36861593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