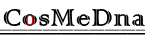在《方法论》(1637 年)中,法国哲学家和科学家勒内·笛卡尔(René Descartes )在他的第一部出版作品《论方法论》(Discourse on Method,1637 年)中结合了一本知识分子自传和对他将在他的《沉思》(1641 年)和《哲学原理》(1644 年)中更严格发展的系统的流行介绍. 冥想从对过去所有信念的怀疑开始的激进尝试,但找到了一个反对怀疑自我作为一种思考事物的存在的命题。然后它使用这个最初的确定性作为论证上帝存在的基础,思想和身体是不同的,如果我们只同意清晰明确的想法,我们就可以在科学中获得确定性,前提是我们首先表明上帝不会在这些想法上欺骗我们。《原则》以《沉思录》中阐述的形而上学和认识论为基础,雄心勃勃地尝试提供对整个世界的科学解释。
童年和正规教育(1596–1618)
笛卡尔于 1596 年 3 月 31 日出生在都兰的拉海耶村,在他外祖母的家里,他在 1597 年母亲去世后与外祖母住在一起。他的父亲约阿希姆·笛卡尔是绅士成员和布列塔尼议会的一名议员,其职责要求他每年在雷恩度过几个月。当仁é四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再婚,搬到雷恩; 任正非é和两个哥哥姐姐依然和他的祖母。我们对他早年的情况知之甚少,但他似乎从未与父亲亲近,无论是作为孩子还是成人。他的祖母在他大约十四岁时就去世了。
十,笛卡尔进入皇家学院的La FL è车,目前两年前由亨利四世和耶稣会运行。该计划的前五年以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理想为指导,因此致力于研究拉丁语、希腊语和古典文学(尤其是拉丁语和西塞罗的作品)。过去三年致力于许多学科的教学,包括:
Thomistic-Aristotelian 哲学,包括辩证法(Aristotles Organon)、自然哲学(Aristotles Physics ; On the Heavens [ De caelo ];以及On Generation and Corruption [ De generatione et corruptione ], book I);数学(算术、几何和应用数学中的主题,如天文学);形而上学(亚里士多德的《论生成与腐败》,第二册;论灵魂[ De anima ];和形而上学);道德哲学(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和耶稣会疑犯的著作)。对亚里士多德和阿奎那的研究广泛使用了 16 世纪晚期和 17 世纪早期的评论,尤其是科英布拉大学耶稣会士的评论。有时,课程忽略了亚里士多德思想难以与基督教教义相协调的方面。学生们没有阅读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的神学部分,其遥远的上帝不是宇宙的创造者,而是阅读公元一世纪的神创论论文,论世界(De mundo),该论文被错误地归于亚里士多德。在其他情况下,面临的问题。托马斯·阿奎那 (Thomas Aquinas) 将亚里士多德关于灵魂的教义解释为与基督教关于个人不朽的教义相一致。在十六世纪彼得罗·庞波纳齐( Pietro Pomponazzi)很有说服力地辩称,阿奎那误读了亚里士多德,而亚里士多德实际上认为灵魂是会死的。Pomponazzi 本人并没有否认永生。他的官方立场是,哲学既不能证明也不能反驳灵魂的不朽,但这一启示使之确定无疑。然而,由于他倾向于将亚里士多德的观点等同于人类理性在没有启示的情况下自然会达到的那些观点,因此他危险地接近了与阿威罗主义传统相关的双重真理学说——哲学真理和神学真理可能会不可调和地冲突。耶稣会课程要求其学院的教师攻击这些评论员的权威。
笛卡尔可能从这些争论中得出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论。当他开始提出自己的知识论时,他写道:“每当两个人对同一件事做出相反的判断时,肯定至少有一个是错误的,而且似乎他们都没有知识。因为如果一个人有一个确定的、明显的论点,他将能够以一种最终说服他的智力的方式向另一个人提出它”(Adam and Tannery X, p. 363)。关于永生是否与亚里士多德的灵魂理论一致的争论的持续存在可能鼓励笛卡尔发展他自己的反亚里士多德理论。他对数学的研究也可能鼓励了对亚里士多德自然哲学的怀疑。在 La Flè老师们使用了耶稣会数学家克里斯托弗·克拉维乌斯( Christopher Clavius) (1538 – 1612) 的著作,他认为数学优于其他假定的科学,因为它成功地消除了所有怀疑,而其他所谓的科学则通过以下方式证明了它们的不确定性他们无法达成共识。
当时,耶稣会学院主导了法国的中等教育,对一代政治、哲学和宗教领袖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打击新教异端,但他们也回报国王的支持,捍卫他对绝对权力的主张。大学要求完全沉浸在耶稣会教育计划中,几乎不与外界接触(包括父母)。笛卡尔对这种教育有复杂的感情。在他关于方法的论述中,他对此持批评态度,声称它没有为他提供他所希望的——对生活中一切有用的清晰和确定的知识——却反而让他被诸多疑惑和错误所困扰。在他看来,他从学习中得到的只是越来越意识到自己的无知。尽管如此,他还是谨慎地说,他认为他的学校为他提供了与当时一样好的教育,后来他将这所学校推荐给了他们孩子的朋友。
笛卡尔完成了在佛罗里达州的La节目è在1614在切话语,他马上写了,因为他是老足以让他的老师的控制,他完全退出字母的研究和追求知识的掌握情况,他可以在自己身上既找不到或在世界的大书中。这并不完全正确。我们对他在 1614 年至 1618 年间的所作所为知之甚少,但我们确实知道他于 1616 年在普瓦捷大学完成了法律学位。他最早的传记作者阿德里安·巴耶 (Adrien Baillet) 报道说,笛卡尔度过了第一年离开 La Flè 后che 位于巴黎郊外的一个村庄 St. Germain-en-Lay。那里的皇家花园拥有非凡的雕像,旨在移动、播放音乐甚至说话。看到这些机器模仿有生命的、有智慧的生物的行为,可能有助于使笛卡尔后来的学说变得合理,即动物只不过是机器。
非正式教育:遇见贝克曼 (1618–1619)
1618 年夏天,笛卡尔离开法国前往荷兰加入拿骚的莫里斯军队。他的法律研究更自然地会导致他在法律或政府方面的职业生涯,这是他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多次考虑的可能性。但在 1618 年,军事生活更加诱人,有机会旅行和了解科学理论的实际应用。莫里斯鼓励科学研究,并聘请了荷兰著名科学家之一西蒙·史蒂文( Simon Stevin),监督他的军队在军事技术方面的教育。史蒂文的科学成就包括对亚里士多德理论的实验反驳(预期伽利略伽利莱),即重物体比轻物体下落得更快,以及他发现了“流体静力学悖论”:液体向下的压力仅取决于物体的高度和底部。它的容器,与它的形状无关。作为一名军事工程师,史蒂文开发了一种水闸系统来淹没田地,为荷兰人提供了一种抵御入侵军队的关键(如果是得不偿失的)手段。1618 年,荷兰人在争取从西班牙独立的战争中仍处于休战期,因此笛卡尔没有看到任何战斗。在这段时期的一封信中,他写道,他花了很多时间学习绘画、军事建筑和荷兰语。
这最后一个野心的动力是他与艾萨克·贝克曼的相遇1618 年 11 月,他是一位比他年长几岁的荷兰科学家。在给贝克曼的一封信中,笛卡尔将他从懒惰中唤醒,并在脑海中回忆起他几乎忘记的知识,并将他带回了认真的追求。到 1619 年春天,笛卡尔正在考虑两部作品,一部是力学的,另一部是几何学的。在他的热情中,笛卡尔写信给比克曼,并承诺将他拥护为“我的研究的推动者和第一作者”(Adam 和 Tannery X,第 162 页)。他们后来的关系就没有那么亲切了。1630 年,笛卡尔要写信给贝克曼,抱怨这位年长的人自称是笛卡尔的老师。虽然他们后来和解了,但笛卡尔没有在《话语》中提及贝克曼。
为什么笛卡尔与贝克曼的相遇如此重要?首先,正如 Beeckman 所说,他们都希望“以精确的方式将物理与数学结合起来”(Gaukroger 1995,第 69 页)。Beeckman 多年来一直以这种方式解决问题,很高兴找到一位志同道合的同事。一个结果是笛卡尔写的一篇关于音乐的短篇论文,试图找出组合起来令我们感到愉悦的各种声音之间的数学关系。他可能在遇到贝克曼之前就开始撰写这篇论文,但他在 12 月完成并于1619 年元旦作为礼物送给了贝克曼。
他们更正常的互动模式是,比克曼会用力学或相关领域的问题给笛卡尔设置问题,并邀请他解决。例如,Beeckman 认识到在虚空中自由下落的物体会均匀加速。所以他提出了以下问题:假设一个在虚空中运动的物体将永远运动(与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相反,贝克曼假设了惯性原理的一个版本)。进一步假设(再次与亚里士多德相反),在下落的石头和地球之间存在空隙,并且石头在给定的时间内覆盖了给定的距离。到那时它会下降多少?早在 1604 年,伽利略就已经制定出正确的自由落体定律物体的数量,这意味着下落物体的速度与它下落的持续时间成正比,但他直到 1638 年才公布这个结果。笛卡尔得出结论,速度与所覆盖的距离成正比,这是伽利略犯的错误也是他第一次尝试解决问题。这里重要的是,Beeckman 鼓励笛卡尔参与伽利略计划,发现控制物体运动的定律,可以用数学公式表达。
贝克曼影响笛卡尔的另一个领域涉及他根据组成宏观物理现象的微观粒子的机械特性来解释宏观物理现象的程序。这个程序——现在通常被称为“微粒学假设”或“机械哲学” ——与古代原子论有联系,但在重要方面与原子论不同。它没有假设组成粒子是不可分割的,而且在笛卡尔要发展它的时候,它也没有假设存在虚空。此外,古代原子论将原子的大小和形状视为主要的解释因素,而粒子学家则强调粒子的速度和运动方向。
Beeckman 为笛卡尔设置的一个问题是用粒子术语解释 Stevin 的流体静力学悖论。笛卡尔假设水柱的重量可以减少为其粒子向下运动的趋势所施加的力,并且容器底部的每个水粒子都通过一条独特的线与表面上的粒子相连力(运动趋势)沿其传递的粒子。令人惊讶的是,笛卡尔认为这种解释有效。表面面积和底面面积相等的情况似乎是合理的,但在最需要解释的情况下,即表面面积小于(或大于)底面面积的情况下,这似乎是合理的。
这些例子让我们对笛卡尔可能已经包括在他正在考虑的力学工作中的那种研究有了一个想法。他在数学方面的工作似乎预示着他发现了解析几何,这是他对科学最持久的贡献。在 1619 年 3 月给贝克曼的一封信中,笛卡尔兴奋地写道,他希望发现“一门全新的科学”,它将“提供所有可能方程的一般解,涉及任何种类的数量,无论是连续的还是离散的”(亚当和制革厂 X,第 156 页–157)。解决这些几何或算术问题的途径似乎涉及使用复杂的工具,“比例罗盘”。笛卡尔设计的圆规不仅解决了将一个角分成任意数量相等的较小角的问题,而且还解决了不同复杂程度的三次方程。他还没有制定他将在他的几何学中发展的使用代数方法解决几何问题的程序。但他已经朝着统一算术和几何迈出了一步。
在德国寻找职业(1619–1620)
1619年春天,三十年战争刚刚开始,笛卡尔启程前往德国,加入天主教联盟领袖巴伐利亚的马克西米利安的军队。在话语中他告诉我们他作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参加了斐迪南二世的加冕典礼。返军途中,寒冬将他困在一个无人倾诉,也懒得找麻烦的地方。一整天都关在有暖气的房间里,他一个人在思索。这种孤立产生了他生命中两个主要转折点中的第一个。在 Baillet 看到并保存的一份现已遗失的文件中(显然是释义和引用的混合体),笛卡尔在 1619 年 11 月 10 日写道,虽然“充满热情”,但他发现了“一门奇妙科学的基础”。笛卡尔留下了关于这一发现是什么的相互矛盾的迹象。
17 年后写成的《话语》中的记述暗示笛卡尔的发现涉及一个决定,即要在科学中做出坚定的判断,他将不得不摆脱他以前的所有观点,并在新的基础上重建他的信仰体系,不接受任何东西他以前一直相信,直到他用理性来证明它。他相信的太多东西是基于他年轻时不加批判地接受了他人的意见。巴耶特看到的文件——笛卡尔报告说他在 11 月 10 日晚上做过的三个梦的描述,可能是在事件发生后不久写的——并没有暗示他要摆脱过去所有的观点。笛卡尔最早的方法论工作也没有,心灵方向的规则,他显然是在这个时候开始的。
三个梦中,最重要的是最后一个。在那个梦中,笛卡尔在桌子上发现了两本书。他将其中一个描述为字典;另一本是诗集。当他打开这本选集时,他发现了 Decimus Magnus Ausonius(约 310 – 395)的一首诗,开头是Quod vitae sectabor iter?(“我的人生该走哪条路?”)笛卡尔说,当他还在睡梦中时,他意识到自己在做梦并开始解释他的梦。他将奥索尼乌斯的这首诗的发现解释为表明他必须为自己的生活选择正确的方向。而字典,我们可能应该认为它更像是一部百科全书,他将其解释为代表所有科学的集合。他的整个梦想表明他应该选择的人生道路是追求科学并证明它们的基本统一性。这一时期保存下来的一段片段形象地表达了这个想法:“现在的科学都是蒙面的,但如果摘下面具,它们会显得最美丽。
思想方向的规则(早期阶段,1619 年至1620 年)
在笛卡尔死后留下的未完成的作品中,有一部关于方法论的论文,显然他在 1619 年至 1628 年间断断续续地进行了工作:思想方向的规则(简称Regulae)。他打算将Regulae 分成三部分,每部分都包含十二条规则。虽然他只完成了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的一半左右,但这是我们在 1629 年之前的时期最充实的作品。它的部分往往看起来彼此不一致,显然反映了作品构成的不同阶段和缺乏任何统一的修订。尽管如此,这项工作揭示了笛卡尔的发展和后来的思想。我们目前关于其组成的最佳理论——从让-保罗·韦伯 (1964) 和约翰·舒斯特 (1980) 的分析得出的结果——认为笛卡尔首先写了规则四的一部分,也许是在三个梦的夜晚之前,他在那个时期的某个时间完成了第一部分的大部分从 1619 年到 1620 年,然后他将这项工作搁置了几年,在 1626 年至 1628 年期间重新开始工作,当时他添加了规则十二到二十一条。之后,他放弃了工作,原因我们只能猜测。
规则四的后半部分(现在称为“规则 IV-B”,从 Adam 和 Tannery X 的底部开始,第 374 页)叙述了笛卡尔对数学的第一次研究以及他对古代数学家的失望。他在其中发现了许多关于数字的命题,经过自己的计算,他认为这些命题是正确的,并且他的作者通过逻辑论证得出了许多关于数字的结论。但是他们没有解释为什么这些事情应该是真的,或者他们是如何发现它们的。笛卡尔推测古代数学家拥有一种他们隐藏的代数发现方法,因为它使数学真理的发现太容易了。他们担心公开他们的方法会降低人们对他们成就的尊重。
Regulae的第二阶段更加雄心勃勃,旨在制定适用于所有科学的方法论。他说,它们全都是“人类智慧,无论其对象如何不同,它始终保持一致”(Adam 和 Tannery X,第 360 页)。科学是如此相互关联和相互依存,以至于一起学习比单独学习更容易。一个在科学中寻求真理的人首先要做的是考虑如何增加他的“理性之光”,即他与生俱来的认知能力。(“Ingenium”这个词在标题中传统上翻译为“头脑”,Regulae ad directionem ingenii,可能更愉快地翻译为“本能的认知能力。”)否定的,这意味着我们应该只依靠直觉和演绎——也就是说,当我们仔细观察它们时,我们可以清楚地、确定地看到其真实性的命题,不会被我们的感官和想象力告诉我们的东西所迷惑,并且可以通过同样清晰和确定的推理过程从第一类命题中推断出命题。
笛卡尔声称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真正的科学是算术和几何。但他否认这些是我们可以通过直觉和演绎获得绝对确定性的唯一领域。有比大多数人怀疑的更直观的某些真理。他举例说明了他的存在、他的思想以及一个三角形仅由三条线所界定等命题。如果我们正确使用这些真理,而不是将它们与可能的假设混在一起,我们将能够将数学的确定性扩展到其他领域。这是一种攻击,不仅依赖于感官或想象力,而且还依赖于“可能的三段论”的学术使用,其前提只需要大多数智者的支持即可被接受。
积极地,笛卡尔的中心信息是我们必须以有序的方式进行研究,逐渐将复杂和晦涩的命题简化为更简单的命题,直到我们得出足够简单的命题,以至于我们可以直观地了解它们,我们可以看到在没有其他命题帮助的情况下,他们的真理。一旦我们完成了这个还原,我们就可以一步一步地回到我们最初希望确定其真假的命题。假设问题是找到 3 到 48 之间的三个平均比例。我们可能对答案没有任何直觉。但是,如果我们寻找这些数字之间的单一平均比例 12,那么我们会将原始问题简化为更易于管理的问题,找到 3 和 12 之间以及 12 和 48 之间的平均比例。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出 3 是to 6 as 6 is to 12, and that 12 to 24 as 24 is to 48. 看到这使我们能够看到 6、12 和 24 是所寻求的数字。
这里的视觉隐喻是故意的。“Intuitus”,翻译为“直觉”的拉丁语名词源自动词“intueri”,其基本参考是视觉感知,尽管它在古典拉丁语中通常被扩展为考虑和沉思的心理行为。笛卡尔认为,通过将直觉与视觉进行比较,我们可以学习如何更好地利用我们的直觉力。如果我们试图同时观察许多物理对象,我们将无法清楚地看到它们。同样,如果我们试图在一个单一的思想行为中处理许多命题。我们可以通过一次将注意力集中在一个简单的物体上来改善我们的身体和精神视力。
笛卡尔强调,直觉不仅是我们对推理前提的了解所必需的,而且是推理过程本身所必需的。要获得关于推理结论的科学知识,我们不仅必须直观地了解推理的前提,还必须直观地了解前提与结论之间的联系。要通过演绎知道 2 + 2 = 3 + 1,我们不仅必须看到 2 + 2 = 4 和 3 + 1 = 4,而且我们的结论必然来自这些前提。我们无法避免依赖直觉,与经院哲学一起坚持我们的论点具有形式有效性。笛卡尔接受了对三段论推理的经典怀疑论批评:它作为获取知识的手段是无用的,因为论证的形式化——添加一个被抑制的条件或全称前提来将一个韵母转换成一个形式上有效的三段论——没有任何作用。如果被压抑的前提是明显的,则论证的有效性是不必要的。如果被抑制的前提不明显,那么推理的形式化所做的就是增加需要证明的假设的数量。
流浪者年代(1621–1625)
在产生Regulae最早阶段的最初能量爆发之后,笛卡尔似乎将项目搁置了一段时间并且没有产生任何重要的工作。他到处旅行,回到法国,访问意大利(可能不止一次),最后回到法国在巴黎长期逗留。他卖掉了他从母亲那里继承的财产,用所得收益来获得适度但固定的收入。这使他摆脱了谋生的需要。他大概是去意大利洛雷托朝圣,兑现了三梦一夜之后的承诺。显然,他经过佛罗伦萨时并没有拜访伽利略。但在此期间他似乎结识了马林·梅森 (Minims 的成员,居住在巴黎的一个修道院),他分享了他对数学和新机械哲学的兴趣。
这些年来,梅森专注于反对米歇尔·德·蒙田 (Michel de Montaigne)所流行的激进的、皮浪式的怀疑论,他认为这是对宗教和社会的严重威胁。他的“反驳”,在总结了拉v é RIT é沙漠科学驳LES sceptiques OU pyrrhoniens(本的科学真相; [1625]),向怀疑论者承认我们不能对物理事物的本质有一定的了解,但坚持我们可以对数学(包括几何光学等应用数学学科)有一定的了解。他还认为,感官经验为物质世界的知识提供了基础,只要它声称只是对现象的知识,而不是事物的本质。如果笛卡尔在 1620 年代与梅森交往之前不熟悉皮浪式的怀疑论挑战,那么他那时一定已经意识到了。
Libertine Paris 的生活(1625–1628)
当笛卡尔于 1625 年返回巴黎时,他遇到了一个有争议的知识分子场景。不仅是男人喜欢的梅森关注皮浪主义的威胁,但巴黎刚刚看到的钍审判é ophile德维奥,新教的诗人,其作品包含Lucretian原子论,淫荡的庆祝活动,和自由的思想的倡导建议。就在几年前,朱利奥·切萨雷·瓦尼尼 (Giulio Cesare Vanini) 因传播据称是唯物主义的教义而在图卢兹被烧死。这些和其他自由思想家被称为“放荡者”,他们被指控持有可耻的宗教观点,并过着放荡、享乐的生活方式——他们否认(或怀疑)来世的自然结果。一个梅森在这一时期的项目之一是宗教异端一个漫长的攻击,LIMPI é牛逼é DES d é istes,ATH é ES等libertins德CE临时工(的自然神论者,无神论者,和我们时代的放荡者的不敬[1624 ])。毫无疑问,梅森使用了一个非常慷慨的无神论标准,估计仅在巴黎就有至少 50,000 名无神论者(当时整个城市的人口只有大约 300,000 人)。
无论威胁是否像梅森声称的那样严重,它都引发了一种试图压制任何非正统观念的反应。1624 年,三个人试图举行一场公开辩论,他们将挑战亚里士多德自然哲学中的各种论点。拟议的辩论显然引起了相当大的公众兴趣,因为据说它吸引了八九百人。但是索邦大学的神学院阻止了它的发生。这些人因死亡的痛苦被驱逐出巴黎;该议会禁止任何人持有或教授论文“与古代被认可的作者相反,也不得举行任何未经神学院医生批准的公开辩论”(Gaukroger 1995,第 136 页)。违反此法令的惩罚将是死刑。
笛卡尔在他生命的这个阶段似乎没有参与这些文化战争。显然,他的主要关注点是解决几何光学问题和恢复Regulae 的工作。在巴黎这些年的某个时候,他显然发现了称为斯涅尔定律的折射定律:当光从一种介质传递到另一种介质时,入射角的正弦与折射角的正弦成正比。(虽然威勒布罗德·斯内尔在笛卡尔之前发现了这条定律,笛卡尔的发现独立于斯内尔的发现。)解决光学中的一个实际问题需要了解这条定律,即找到无弹性曲线,透镜表面必须具有收集平行光线的形状光变成一个焦点。这些知识对于设计能够提供比现有望远镜更清晰图像的望远镜是必要的。笛卡尔在做这项工作时,望远镜是最近发明的,只能追溯到他在 La Flèche 的那几年。笛卡尔对新科学仪器扩展我们对自然的认识的潜力感到非常兴奋。
在他于 1637 年与Discourse on Method一起发表的关于光学的论文中,笛卡尔试图从微观力学上解释斯涅尔定律,根据参与光线传输的粒子的运动趋势和运动定律,他认为这些定律适用于运动的倾向以及运动的倾向。他还提出了一种解决无塑性曲线问题的方法:镜片应具有双曲线形状。他在光学方面的新研究也对他对Regulae 的修订产生了影响,为他提供了一个使用该方法将其范围从数学扩展到物理的例子。
后来的规则(1626–1628)
根据我们最好的组成的现有理论Regulae,一个变化,笛卡尔提出,当他回到这项工作是为了增加该方法的两个例子在现在一般称为“第八条法则-C”的通道规则八(亚当和制革厂 X,第 393 – 396 页)。
第一个例子处理确定无弹性曲线的问题。早先的规则规定,我们逐渐将复杂和晦涩的命题简化为更简单的命题,直到我们达到对最简单命题的直觉,然后我们可以追溯我们的步骤,直到我们获得对我们最初希望知道的命题的直觉知识。遵循此建议的人应该首先看到,确定无塑性线取决于确定折射角和入射角之间的关系。他将无法通过推测、诉诸经验或向哲学家学习来确定这种关系。但是如果他意识到这种关系取决于媒体的差异所带来的角度变化,他就会取得进步,并且这种变化取决于光线如何穿透透明介质。了解它如何穿透该介质需要了解光的性质。最后,理解光需要了解一般的自然力量。
在这段话中,笛卡尔没有说自然力量是什么。在这里他只说,因为这是“整个系列中最绝对的东西”,调查中最基本的项目,不依赖于任何更基本的东西,这是我们可以直观地掌握的东西。一旦我们这样做了,我们将能够追溯我们的步骤——利用我们对自然力量的理解来理解光的本质,我们对光的理解来理解它如何穿透透明介质,以及我们对光穿透的理解来理解介质的变化会改变光线的路径——直到我们最终能够回答关于无弹性曲线的问题。在Regulae的其他地方(Adam 和 Tannery X,第 402 页),笛卡尔建议理解自然力量的概念需要反思物体的局部运动——这个想法显然是物体总是通过将运动从一个物体传递到另一个物体而相互作用接触。
直觉和演绎的频繁通话Regulae容易建议-很多人都倾向于相信什么其他原因呢-笛卡尔的科学方法完全是先验的。但事实并非如此,即使在Regulae中也是如此。尽管笛卡尔在规则 8-C 中说我们不能通过经验确定折射角与入射角的关系,但原因似乎是这个问题太复杂,无法通过诉诸经验来解决。“我们可以有一定的经验知识,”他说,“只有完全简单和绝对的事情。” 我们可以推断,我们从经验中得出在这种情况下最简单的直觉——什么是自然力量,在这种行为可以立即理解的情况下,身体如何自然地相互影响。
当笛卡尔在光学中发展他的光理论时,他经常使用经验类比。光从发光体传输到照明物体,就像阻力通过盲人的手杖从路径上的物体传输到他的手。光亮表面的光反射就像网球从不透水的表面反弹时的运动。折射就像网球遇到可渗透表面时的运动。并非我们观察到的所有事物都像这些类比案例一样容易理解。铁屑在磁铁作用下的运动是神秘的。但是,笛卡尔科学计划的一部分是尝试通过将这些现象简化为易于理解的其他现象来理解这些现象。就笛卡尔诉诸共同经验来支持这些直觉而言,
笛卡尔在回到规则八时添加的另一个例子,他描述为“最值得注意的”。他说,每一个喜欢真理的人,都应该在他的生命中设定一次(semel in vita),确定人类理性能够知道哪些真理以及哪些问题超出了我们的认知能力的任务。这将防止他总是不确定头脑可以做什么,并避免他在我们的官能无法处理的事情上浪费时间。承担这项任务的人会发现,在理智之前,没有什么是可以知道的,因为所有其他事物的知识都依赖于它,而它并不依赖于对它们的知识。但是,尽管笛卡尔断言了纯粹智力的优先性,但他也承认,除了智力之外,我们还有其他知识工具。在规则 8-C 中,笛卡尔说有两种这样的工具:想象力和感官。在接下来的文本中(从 Adam 和 Tannery X,第 396、26 页,到规则八的结尾,通常被称为“
这段经文最引人注目的是它与后来众所周知的文本的不同之处,后者在其他方面非常相似。规则八中的三次(一次在八-C中,两次在八-D中)笛卡尔使用了短语“semel in vita”来指代每个想要很好地使用他的认知能力的人都应该在他的一生中进行一次的项目。每次他用洛克式的术语描述这个项目时,都会有细微的变化,作为一个需要我们确定人类理解极限的项目。笛卡尔在第一次沉思的开篇中使用了相同的短语“semel in vita”,也指的是一个人一生应该进行一次的计划。但在冥想项目中,不是确定人类理解的极限,而是推翻他多年来随意获得的所有意见,因此他可以从坚实的基础重新开始。三年后,在《哲学原理》中,他使用了同样的短语“生活中的 semel”,再次呼吁所有追求真理的人对任何过去的观点都予以同样的推翻,因为他们在其中发现了哪怕是最小的不确定性怀疑。当笛卡尔在《沉思录》中发展这个项目时,很明显,在被拒绝的意见中,至少是暂时地,包括那些甚至涉及最简单的数学真理的意见,这些在规则中是确定性的范式。为了获得绝对的确定性而进行的彻底怀疑的呼吁——笛卡尔已发表作品的最大特点——在《规则》中是没有的。
在荷兰寻求孤独 (1629–1633)
在巴黎年末,笛卡尔参加了一次会议,该会议成为他生命中的第二个重大转折点。巴黎的许多主要知识分子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在教皇大使的宫殿举行。演讲者是一位名叫尚杜的化学家/炼金术士,他抨击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是化学的不充分基础,并显然提出了一种机械方法来代替它。相反的是,我们可以从亚里士多德的批评这一禁令在1624年预料,大多数在场的人,包括谁梅森和红衣主教皮埃尔·德·乙é RULLE,收到Chandoux的讲话很好。笛卡尔没有。
乙érulle 注意到笛卡尔没有分享这个团体的热情,并问为什么。在礼貌地试图为自己的想法找借口后,笛卡尔对尚杜进行了扩展批评,称赞他希望将哲学从“学生的困惑”中解救出来(Baillet,第 69 页),但指责他用某些东西代替它只是可能。他争辩说,如果只允许可能的论据,就很容易使假的显得真,真假。然后,他向公司提出挑战,让他举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的例子。当他们这样做时,他提出了十几个可能的论据,旨在证明其错误。然后他要求他们举出一个明显的谎言的例子。当他们提供一个时,他用另外十几个可能的论据证明了这个谎言是可信的。然后,这群人问他是否有任何可靠的方法可以避免诡辩。他回答说,他知道的最确定的方法就是使用他通常遵循的方法,该方法源自数学,他认为足以清楚地证明所有真理。
笛卡尔的辩证别出心裁做他的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基数B é RULLE,谁不愿看到他私下。后来他们见面时,笛卡尔声称如果他继续他的调查,对公众的好处将是可观的。他可以在医学上取得显着改善人们健康的成果,并在机械方面取得成果,从而大大减少人们的劳动。乙é鲁勒回答说,既然上帝赋予笛卡尔这种非凡的才能,他就应该感谢上帝和他的同胞们来充分利用它。一段时间以来,笛卡尔一直在考虑离开巴黎。这次谈话打破了平衡。他决定在荷兰定居,在那里他会找到一个更适宜的气候,更重要的是,他可以在那里安静地进行冥想,而不会被朋友不断地打扰。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笛卡尔将激进的怀疑主义视为一种严重的可能性。他一定知道关于皮浪主义和一些皮浪主义文献的辩论。但是,Baillet 对 Chandoux 事件的描述和笛卡尔自己对 1631 年事件的描述都表明笛卡尔的认识论与Regulae的认识论非常相似:对经院哲学和对可能论证的任何依赖不屑一顾,对数学和数学的确定性充满信心。他以他在数学上的发现为蓝本的方法。在荷兰的最初几年,笛卡尔对这些问题的态度似乎发生了变化。
我们从 1630 年 11 月给梅森的一封信中得知,笛卡尔搬到那里后不久(可能在 1628 年至1629 年的冬天),他开始了他所描述的“形而上学的小论文”,在其中他着手证明“当上帝和我们的灵魂与身体分离时,他们的不朽就会存在”(Adam and Tannery I, p. 182)。这本“小论文”听起来像是《沉思录》的早期版本。那时它显然不完整,我们对其具体内容知之甚少,但从早期给梅森的一封信(1630 年 4 月 15 日)看来,笛卡尔在他任职的头九个月里一直在撰写这篇论文。荷兰人。
在 4 月 15 日的那封信中,笛卡尔还描述了最近开始的似乎不同的“小论文”。为了给自己提供尽快完成它的额外动力,他承诺在 1633 年初之前将它寄给梅森。只需要一个下午就可以阅读。这篇论文显然侧重于物理学。但是笛卡尔说,如果他没有通过首先尝试认识上帝和他自己来接近这些基础,他就无法发现他的物理学基础,并且他已经发现如何以比证明更明显的方式证明形而上学真理几何学。这首次表明笛卡尔试图将物理学建立在形而上学的基础上,特别是一种形而上学,它侧重于对上帝和自我的认识。它还首次表明几何证明可能存在一些缺陷,除了形而上学基础之外,它们可能不如笛卡尔发现的形而上学证明那么确定。
为什么笛卡尔当时认为几何证明可能需要形而上学的基础?4 月 15 日的信包含一个可能的线索。笛卡尔第一次提出了一个令他臭名昭著的学说:永恒真理的创造。他写信给梅森说,在他的物理学论文中,他会讨论几个形而上学的话题;特别是,他会捍卫这样的观点,即数学的永恒真理是由上帝确立的,就像国王在他的王国中制定法律一样,它们完全取决于他,不亚于他的其他创造物。
关于这一学说的含义以及笛卡尔为什么持有它,存在很多争论。但我们目前关心的是它与数学确定性的关系。当笛卡尔在第一次沉思中争辩说,即使是数学真理也会受到怀疑,他并没有援引上帝创造它们的学说。他只是诉诸于上帝是创造他的无所不能的存在的想法,他可以,如果上帝选择了,他创造了如此不完美的人,以至于他的认知机器可能会让他误入歧途,即使是在他看来最明显的事情上。在信件和其他地方,我们可以看到笛卡尔认为对全能的正确理解会得出结论,它需要确定永恒真理是什么的能力。但是笛卡尔知道这是一个不寻常的、有争议的全能概念,他没有在第一次沉思中使用它。在《话语》中,当他要证明他对数学的怀疑是正确的时,笛卡尔会写道:“我不知道我是否应该告诉你我[在荷兰]的第一次沉思,因为它们可能过于形而上学和每个人的口味都不常见。”
自阿奎那以来,经院哲学中的主流观点是,上帝有权通过他的意志来决定哪些偶然的真理是真实的,但他的意志并不决定哪些必然的真理是真实的。这些真理应该建立在上帝的智力、他的想法,而不是他的意志之上。第一次沉思的沉思者从一个刚开始进行哲学思考的人的角度来解决什么事情会受到怀疑的问题,他大概对上帝的全能意味着什么持有传统的看法。而且,干扰他受造物的认知能力的能力似乎并不需要上帝拥有创造永恒真理的能力。一定,
尽管如此,怀疑论者认为上帝的力量可能会扩展到永恒的真理,并使用这种想法来怀疑数学和我们可能认为必要的任何其他真理。在他对雷蒙德·塞邦德的道歉中,蒙田对皮浪式怀疑论的论据之一涉及这样的主张,即由于上帝的力量是不可思议的伟大,如果我们说有些事情他不能做,我们就会不敬地说话。蒙田建议说上帝不能做的事情是不敬虔的,其中包括使十倍于二十不等于二十,背弃他的话,使一个活过的人没有活过。蒙田并没有说上帝创造了永恒的真理。但他确实说,声称上帝不会使人虚伪是人的傲慢通常被归类为永恒的真理。这一类不仅包括简单的数学真理,还包括形而上学的真理(如“过去是一成不变的”和“虚无之物”)和道德真理(如“一个完美的人不会违背他的诺言”) . 他用这些不敬和傲慢的指责来证明他的主张是正确的,即我们应该暂停对一切事物的判断,包括这些所谓无可争辩的事实。
笛卡尔同意蒙田的观点,即如果我们说上帝不能做某事,我们就没有公正对待上帝的力量。“我们可以断言,上帝可以做我们能做的一切,但不能说他不能做我们无法做的事”(亚当和制革厂 I,第 146 页)。如果说上帝的能力仅限于我们所能理解的范围,那将是轻率和不尊重的。笛卡尔不想说上帝可以使永恒的真理变为假。它们是不可变的。但它们是不变的,因为上帝的旨意是不变的。因此,到 1630 年春天,笛卡尔认为有必要在形而上学中建立物理学(包括数学的真理),他对这种需要的看法与他认为上帝的力量是不可思议的伟大的观点有关。他认为他有办法完成这个接地,于是他开始,可以做到这一点的冥想。
世界(1629–1633)
笛卡尔从未发表过他在通信中称为“世界”(或“我的世界”)的物理学论文,但他在他的光学(1637)和气象学(1637)和哲学原理(1644 )中使用了其中的材料)。而工作的部分在他死后出现了:一个标题下的世界报,欧特质é德拉LUMI è重(世界,或伤寒论轻[1979分之1664]),它再现了论文的开始,另一个名为特质é德男士(《人论》[1662/1972]),复制了它的后一部分。在这里,按照 1630 年代初期的预测,整篇物理论文将被称为“世界”,而标题“光论”将指的是 1664 年出版的开篇部分。
世界起源于笛卡尔对解释幻日问题的关注,幻日现象有时会出现在太阳晕中,由阳光通过大气中的冰晶折射而引起。1629 年夏天,一位朋友向他展示了对这种现象的描述,并问他对此有何看法。笛卡尔搁置了他关于形而上学的论文的工作,看看他能做出什么:
我的头脑不是那么强大,我可以同时将它用于许多任务,并且由于我除了通过长期的各种考虑之外从未有过任何发现,所以当我想研究某个特定方面时,我必须全身心地投入到一个主题中。它”(亚当和制革I,第22页。- 23)。
他对幻日现象的好奇心使他首先研究了一般的气象现象(包括彩虹,大气中的另一种折射效应),然后进行了令人难以置信的雄心勃勃的项目,即解释“自然界的所有现象,即整个物理学.”
《光论》首先论证了我们对某物的视觉感觉与产生这种感觉的物体中的事物之间可能存在差异。他声称,普遍的观点是,我们的想法完全就像它们产生的对象一样。但是有很多经验应该对此表示怀疑。例如,在声音的情况下,大多数哲学家认为我们听觉的原因是空气中的振动,这与那些听觉完全不同。笛卡尔提出光也存在类似的情况。
发现光的本质的第一步是确定我们所知道的产生光的物体。这些似乎是星星和火。由于星星太遥远而不易观察,笛卡尔将注意力集中在火上。当我们看到火燃烧一块木头时,我们观察到它使木头的微小部分运动并将它们彼此分开。它将最小的颗粒转化为火、空气和烟雾,并将较大的颗粒作为灰烬留下。经院哲学家可能认为,除了这些机械过程之外,还涉及一种火的形式或一种热的性质。但是笛卡尔(应用奥卡姆剃刀)将自己限制在他认为必须是过程的一部分的范围内,并且没有假设任何不必要的东西来解释这些现象。由于一个物体除了通过自身运动而移动另一个物体是不可想象的,因此笛卡尔推断火焰的物体由小到无法观察但移动得如此迅速的粒子组成,尽管它们的尺寸很小,但力它们作用于木材的强度足以分散其颗粒。火焰粒子的运动会导致火焰产生的光和热量,这取决于它们遇到的感觉器官。但在这两种情况下,原因和想法之间都没有任何相似之处。火焰粒子的运动会导致火焰产生的光和热量,这取决于它们遇到的感觉器官。但在这两种情况下,原因和想法之间都没有任何相似之处。火焰粒子的运动会导致火焰产生的光和热量,这取决于它们遇到的感觉器官。但在这两种情况下,原因和想法之间都没有任何相似之处。
笛卡尔观察到,自然界中没有任何地方是不变的。他认为燃烧所涉及的变化并不罕见:在许多情况下,可观察到的变化的原因在于不可观察的粒子的运动。机械哲学的核心原则是,所有物理变化都可以归结为物体的位置变化,如果不是大到可以观察到的物体,那么小到无法观察的物体。物体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其组成粒子的大小、形状和运动。
笛卡尔区分了三种元素,他称之为“火”、“气”和“地”。这些不能与传统上所谓的元素或通常所谓的熟悉物质相提并论。火是一种非常微妙的液体,由最小、移动速度最快的粒子组成,这些粒子没有确定的大小或形状。这允许它们填充其他元素的粒子之间的间隙,并且不需要允许空隙的存在。空气也是一种微妙的液体。与地球相比,它的粒子小而运动快,但与火相比,它的粒子大而运动缓慢。它们具有确定的大小和形状;几乎所有的都是圆形的。地球的粒子是最大的,几乎没有运动。笛卡尔强调,他没有将热与冷、潮湿与干燥的传统特性归因于他的元素。他通过诉诸物体或其组成粒子的大小、形状和运动,将这些品质本身需要解释。
在解释了他的物理学的基本要素之后,笛卡尔让我们想象上帝在空间的某个地方创造了一个新世界,仅由这种物质构成,并且仅通过不同的物质将这个世界上的不同物体彼此区分开来。他对问题的不同部分提出了动议。这个想象世界的初始状态是没有秩序的。笛卡尔的计划是展示一个像我们这样的世界如何能从这种混乱中出现,只要上帝在创造这个世界时建立的自然法则。(当然,创世纪告诉我们我们熟悉的世界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笛卡尔声称只对探索上帝可以做到的其他方式感兴趣。)
笛卡尔在这里使用的语言——上帝建立了自然法则——让人想起他在给梅森的信中使用的语言,在那里他说上帝建立了永恒的真理(称为“自然法则”)作为一个国王建立他王国里的法律。与国王的比较表明这一行为具有任意性,也可能表明法律可能会发生变化。笛卡尔想要任意性的暗示,但他不想要可变性的暗示。在 1630 年写信给梅森时,他预计梅森在宣传笛卡尔的观点时可能会遇到反对意见(笛卡尔鼓励他这样做):
他们会告诉你,如果上帝确立了这些真理,他可以改变它们,就像国王制定法律一样。必须回答:是的,如果他的意志可以改变。—— “但我理解它们是永恒不变的。” -我让上帝同样的判断”(亚当和制革我,第145页。- 146)。
在 1630 年的通信中,笛卡尔援引上帝意志的不变性来解释永恒真理的不变性。在《世界》中,他用它来为自然法则提供内容。
上帝,“每个人都必须知道”,是不可变的。(据推测,这可以通过 1629 年关于形而上学的论文中上帝完美的论证来建立。)这意味着他总是以相同的方式行事。这反过来又要求他继续以他创造它们的方式保存他创造的物体。这并不意味着事情不会改变。相反,由于上帝在创造这些事物时赋予其中一些运动,这意味着他保留了这种运动。这一事实,再加上虚无的存在,意味着当身体开始运动时,身体也开始通过与其他身体的相遇而改变和多样化他们的运动。
笛卡尔声称从上帝的不变性中推导出三个主要的自然法则:(1)物质的每一部分总是继续以相同的状态存在,只要与其他物体的相遇不会使其发生变化。(2) 当物体相互推挤时,运动的总量保持不变(一个物体不能增加另一个物体的运动,而不会失去与转移到另一个物体一样多的自身运动)。(3)虽然物体的运动通常是曲线,但它总是有运动的趋势在一条直线上。因为笛卡尔否认虚空的存在,所以他坚持所有的运动都必须“在某种程度上是循环的”。由于一个物体没有空的空间可以移动,它只能通过移动其他物体才能移动。最终,每个移动体都必须是形成某种闭合曲线的移动体链的一部分。尽管笛卡尔从上帝的不变性中推导出这些定律,他大概是先验知道的,但他也坚持认为它们与我们在经验中发现的非常吻合。他指出,亚里士多德物理学假设只有继续对运动物体施加力,运动才会继续;所以很难解释弹丸运动。
从这些关于物质性质和物质运动规律的假设中,笛卡尔发展了一个理论,关于像我们这样的世界可能如何从他认为上帝最初在假设的新世界中创造的混乱演变而来。由于那个世界是一个充气室,它的部分必须取代其他部分才能运动,而且所有运动都必须在一条闭合曲线上,物质自然会组织成漩涡,大量物质围绕一个中心旋转,像漩涡一样。火元素将倾向于集中在漩涡的中心,构成太阳和星星;地球元素将倾向于形成大簇,围绕它们的漩涡中心旋转,并由第二元素的粒子携带。行星是由这样的星团形成的,彗星也是如此。但是行星仍然处于一个漩涡中,而彗星则通过运动将它们从一个漩涡带到另一个漩涡。这个明显的日心系统不仅意味着地球围绕太阳旋转,还意味着我们的太阳系只是宇宙中众多恒星中的一个,每个恒星都围绕着不同的恒星形成,这些恒星不再像亚里士多德-托勒密宇宙学那样嵌入一个单一的球体中。
笛卡尔接着解释了行星绕轴旋转、卫星(卫星)绕行星运动、潮汐、重量和光的运动。最后他解释为由太阳和它周围的物质自转引起的。这会产生径向压力,该压力从太阳中心沿直线向外扩散。他列举了十几种光的特性,他声称这个理论可以解释:它从发光体的所有侧面传播到任何距离,瞬间,通常是一条直线,但是当它遇到一个物体时会发生反射不能穿透,遇到可以穿透的介质时会发生折射,依此类推。Optics,出版于 1637 年。在另一部著作Meteorology (1637) 中,笛卡尔解释了彩虹和幻日现象。
众所周知,《人论》是《世界》的一部分,尽管它似乎不会在《光论》之后立即出现。我们不知道中间有多少章节缺失,但我们可以从话语第五部分对世界的描述中大致了解它们的预期内容。涵盖的主题包括地球上山脉、海洋、泉水和河流的形成;土壤中金属的形成和田间植物的形成;以及火的性质及其各种特性,例如它能够从燃烧的材料的灰烬中形成玻璃。
《人论》将包括对身体和灵魂的描述,尽管只有处理身体的章节幸存下来。这些章节首先要求我们想象上帝创造了一个由地球(元素)制成的雕像或机器,他打算尽可能地像我们一样制造。正如《光论》试图表明,仅使用笛卡尔所描述的材料和机制,上帝就可以创造出一个看起来与我们一样的世界,因此《人论》试图表明上帝可以仅使用这种方式制造出外观和行为都与人体相似的机器。尽管笛卡尔认为需要归因于理性灵魂的功能是一个例外,特别是语言的智能使用,但他声称对亚里士多德哲学归因于植物人和敏感灵魂的所有动物功能进行了机械解释:消化食物;心脏的跳动;成员的营养和成长;醒来和睡觉;感觉器官对光、声、香、热等的接收;将这些品质的想法传递给大脑;将这些想法保留在记忆中;欲望和激情的内部运动;
我们无法在此深入探讨这些解释,但有两点值得关注。首先,我们从他的信件中得知,笛卡尔在这些年里花了很多时间解剖动物来学习解剖学。无论像《Regulae》这样的作品多鼓励将笛卡尔描绘成一个纯粹的先验科学家,无论这张照片多么公正,很明显,在实践中,笛卡尔认为科学家有必要进行大量的数据收集. 当梅森写道,他知道人们如此致力于推进科学,以至于他们愿意自费进行各种实验,笛卡尔回答说:
如果有这样的人,按照培根的方法,写出天象的历史,为我们准确地描述天体现在的样子,没有任何解释或假设,报告每颗恒星的位置,那将是非常有用的。对其邻居,以及它们在大小、颜色、能见度、亮度等方面的差异。他应该告诉我们这与古代天文学家所写的内容有多大的一致以及有哪些不同之处;因为我毫不怀疑,尽管恒星被称为固定的,但它们的相对位置总是在不断地改变。(亚当和制革厂 I,第 251 – 252 页)
笛卡尔自己经常提出假设来解释现象。但他知道,对现象的令人满意的解释需要对要解释的现象进行良好的描述,而这种描述需要经验探究。他也可能承认,必要的实证调查将由关于现象的最终解释可能是什么的直觉来指导。在这种情况下,他对培根历史的呼吁似乎是基于他的信念,即所谓的恒星并不是真正固定的。
其次,虽然它可能不是很明显,笛卡尔在科学程序世界体现了他的方法,我们可以作为方法的扩展中的规则八-C描述把它Regulae。对确定无弹性曲线的问题的反思说服笛卡尔,解决这个问题需要理解折射,这需要理解光的性质及其传输,并最终理解什么是自然力量。在《规则》中,笛卡尔对自然力可能是什么含糊其辞,只表明它与局部运动有关。当他开始写《世界》时,他的出发点是光学中的一个类似问题,解释幻日,他必须意识到这也涉及理解折射。他已经相信,了解折射需要了解光的本质,而了解光需要了解什么是自然力量。然后他看到理解自然力量的概念需要关于物体性质和运动规律的成熟理论,而正确理解这一理论将使他能够解释天上和上空的各种现象。地球。
伽利略事件及其后果(1633–1637)
笛卡尔从未发表过《世界》,尽管他已经努力了多年,并取得了令他引以为豪的成果。1616 年,教会谴责哥白尼关于地球在运动而太阳静止的学说是错误的和违反圣经的。它禁止一书由Paolo福斯卡里尼教会了这一学说,并暂停哥白尼的在天球的革命“直到它应该予以纠正。” 此外,红衣主教罗伯特·贝拉明在与伽利略·伽利莱的私下会面中,命令他放弃哥白尼的观点。笛卡尔知道哥白尼的观点受到了谴责。他可能不知道伽利略会见贝拉敏。他似乎听说过谣言,尽管受到谴责,但仍有一些人继续“公开地,甚至在罗马”教授哥白尼的观点。
1623 年,一位对伽利略友好的佛罗伦萨红衣主教成为教皇乌尔班八世。与新教皇讨论后,伽利略获准撰写关于哥白尼体系的论文,只要他把它当作一个数学假设,只不过是一个方便的预测设备。伽利略显然决定测试这个许可的限制。他写了一段对话,其中一位参与者为哥白尼理论辩护,另一位参与者为托勒密理论辩护,第三位则扮演了无拘无束的询问者的角色。他在对话中的发言人并没有声称哥白尼理论的确定性。此外,他让他的正统派代表说了算,宣称无论亲哥白尼的论点多么有道理,我们永远无法确切地知道对这些现象的真正解释是什么。上帝以其无限的力量和智慧,可以以多种方式产生这些现象。最后,在序言中,他声称他的工作将日心说视为“对于哥白尼主义,1616 年的禁令并不是出于无知而发布的。经过与审查员的长期谈判,他获得了在 1632 年出版他的《关于两个主要世界体系的对话》的许可。
但事实证明,他的预防措施是不够的。对于细心的读者来说,很明显他跨越了假设性考虑和倡导之间的界限。1633 年春天,宗教裁判所以“强烈怀疑异端邪说”的罪名对他进行了审判。在这种情况下,这种语言的意思是,他提出了与圣经相反的观点,好像它们是可能的,但有人怀疑他是否有定罪形式异端所必需的邪恶意图。6 月被判有罪,他被判处软禁终生,并被要求放弃错误。
1633 年 11 月,笛卡尔写信给梅森,说他想买一本伽利略的《对话录》,他听说这本书是前一年出版的。可当他去找的时候,才知道它已经被没收烧毁了。他非常惊讶,他说,“我几乎决定烧掉我所有的文件,或者至少不让任何人看到它们。因为我无法想象他是意大利人,甚至(据我所知)受到教皇的青睐……可能仅仅因为他想(无疑是他所做的)建立地球的运动”(亚当和制革厂一世,第 270 – 271 页)而被定为罪犯。笛卡尔写道,地球运动的学说与他自己世界的其他部分有着如此密切的联系他无法拆下它而不会使其余部分非常不满意。如果那个学说是错误的,“我的哲学的所有基础也是错误的,因为它们非常明显地证明了这一点。” 几个月后,当他得知伽利略被谴责时,“即使他假装他提出 [哥白尼体系] 只是假设性的”(Adam and Tannery I, p. 270 – 271),他特别担心,因为他采用了类似的设备自己,代表自己仅仅讲述一个关于上帝的故事怎么可能创造像我们这样的世界,同时承认创世记告诉我们他是如何没有创造它。
目前尚不清楚“世界”此时处于哪个阶段。笛卡尔说,如果能及时复制的话,他已经打算把它作为新年礼物送给梅森。也许它比幸存的部分所暗示的更接近完成。有一阵子,笛卡尔寄希望于有办法出版它。也许宗教裁判所的这一行动尚未得到教皇或教会理事会的批准。如果是这样,它背后可能没有教会的全部权威。但最终笛卡尔决定暂时放弃他的论文并采取不同的计划。他决定发表一篇关于方法的半自传性论文,并辅以三篇简短的论文来证明他的方法的力量:光学、气象学,和几何。
在话语上的方法和它的杂文(1637)
笛卡尔在四十一岁时出版了他的第一部作品,他只活了十三年。从此开始了为他赢得现代哲学之父声誉的公共事业。正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的,笛卡尔关于在科学中很好地进行理性和寻求真理的方法的论述部分是自传,但在这方面不太可靠,因为它省略了重要事件(例如他与贝克曼的关系,他的三个梦想,以及他与尚杜的相遇);它将笛卡尔可能只有在以后才拥有的过去的想法投射到过去的想法中(例如推翻他过去的所有观点以在更牢固的基础上重建他的信念的想法);并且对笛卡尔担心可能会导致他的读者提出他不想处理的反对意见(例如永恒真理的创造)的想法保持沉默。笛卡尔自己警告我们不要把他的作品当成自传来看待,他写道,他“只是把它作为一段历史,或者,如果你愿意,可以作为一个寓言”来呈现。笛卡尔希望我们阅读他的作品,因为它具有道德意义,作为模仿或避免行为的例子。
模仿行为的例子将是我们在科学中寻求真理时如何运用理性的例子。笛卡尔提供了四个规则,他说他在这次搜索中发现了足够的规则:
1) 决不接受任何他显然不知道是真的东西,在他的判断中不包括任何东西,除了那些清楚地呈现在他的脑海中以至于他没有理由怀疑它的东西;
2) 把他正在考查的难点尽可能地分成多个部分;
3)有条不紊地进行他的思想,从最简单的对象开始,逐渐上升到最复杂的对象;和
4)使枚举如此完整,评论如此全面,以至于他确信他没有遗漏任何东西。(亚当和制革VI,第18页。- 19)
如此坦率地提出,这些规则可能没有给出足够的方向来非常有用。在 1637 年 2 月给梅森的一封信中,笛卡尔否认有意在《话语》中教授他的方法。他的目的只是谈论它,他的目的是在伴随《话语》的科学论文中是为了展示通过使用它可以实现什么。在大多数情况下,即使是文章也没有打算展示这种方法在起作用。正如笛卡尔在 1638 年 2 月给 Antoine Vatier 的一封信中所解释的那样,“我无法在 [三篇科学论文] 中展示这种方法的使用,因为它规定了一种调查事物的顺序,这与我认为我必须这样做的顺序大不相同。用来解释它们”(Adam 和 Tannery I,第 559 页)。但是笛卡尔对这种概括提出了一个例外。他告诉瓦蒂尔,他在气象学第八章中对彩虹的讨论中给出了该方法的样本。
在那一章中,笛卡尔首先指出彩虹不仅出现在天空中,而且出现在我们附近的空气中,只要太阳照亮空气中的许多水滴。我们从喷泉的经验中知道这一点。他由此推断,彩虹仅来自光线与水滴相互作用的方式,并从那里移向我们的眼睛。之前在气象学中,他曾证明这些水滴是圆形的;他还知道,大概是根据经验,彩虹的出现与水滴的大小无关。这些反思暗示了一项实验,使他能够在他可以控制的情况下近距离检查这种现象。
他在一个大圆瓶中装满了水,并把它摆好位置,这样当他面对太阳时,太阳就会从他身后射进来。然后他将自己定位在与烧瓶相关的位置,以便在其底部观察到一个鲜红色的斑点。他发现从他的眼睛到烧瓶底部的一条线与从太阳到烧瓶底部的一条线形成了大约 42 度角。更何况,不管他怎么动——离烧瓶更近或更远,向右或向左,即使他让烧瓶绕着他的头旋转——只要他的视线和太阳光线之间的夹角保持在42度左右,他总是能在底部看到一个红点。如果他增加角度,红色就会消失。如果他稍微减少它,这个斑点并没有停止着色,而是分成两个不同颜色(黄色,蓝色等)的亮度较低的部分。由此推断,如果那个方向的空气都充满了这样的圆形水滴,那么每一滴水滴上都会出现一个红点,太阳光线与视线的夹角约为42度,形成一个连续的圆圈。的红点。其他颜色的类似圆圈会在稍微锐角的液滴中产生。
通过对烧瓶的进一步实验,笛卡尔发现当光源被阻挡时,红点并没有消失,只要允许光从烧瓶的顶部进入并从底部离开,并且只要其中的某些路径烧瓶没有被堵塞。他推断底部出现红色是由于太阳光线在进入烧瓶顶部时发生折射,从烧瓶背面的一点反射,并在烧瓶底部再次折射当他们离开它向眼睛移动时。他对副弓的产生提出了类似的解释,副弓以大约 52 度的角度出现,颜色以相反的顺序排列。他推断,这源于两次折射和两次反射的结合。
到目前为止,笛卡尔试图解释的现象主要取决于水相对于空气的折射率,他可以准确计算出这个数字。到目前为止,他对现象的解释基本上是正确的。但他仍然没有解释他所说的主要困难:为什么只有那些光线以一定角度折射才会出现某些颜色?为了解决这个难题,他用棱镜进行了一系列实验,棱镜是一种类似的物体,也已知会产生一系列颜色。棱镜与他的烧瓶有很多不同,这些差异使他能够消除烧瓶的某些无关紧要的特征。为了产生光谱,光通过的介质不一定要有曲面,或者光线以特定角度撞击该介质,或者它被反射,或者它被多次折射。但是光必须至少折射一次。
在这一点上,笛卡尔援引了他的光本质理论,即光是空气粒子(元素)的作用或运动,必须将其想象成小球。这些球有两种运动,一种是沿其传播方向,另一种是旋转。当它们撞击眼睛时,不同程度的旋转运动会产生不同的颜色感觉。光线折射时产生的颜色差异源于折射过程赋予光粒子不同程度的旋转运动。(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Gaukroger 1995,第 6 章。)
笛卡尔的这部分解释并不顺利。但是这个例子在许多方面仍然很有趣。首先,它说明了笛卡尔的第二条和第三条规则:将一个复杂的问题尽可能分成多个部分,直到你得到一些简单易懂的东西,然后再回到你最初感兴趣的复杂现象。复杂现象是彩虹。简单的对象是具有彩虹颜色之一的单个水滴。通过使用我们可以近距离观察和操作的简单物体的模型,我们可以确定其被视为具有它所具有的颜色的条件,并且我们可以确定改变这些条件如何可能产生不同的颜色(或没有颜色)一点)。
但是这个例子也警告我们,如果我们使用直觉和演绎的概念来分析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我们需要非常广泛地理解这些概念。我们对简单物体行为的理解涉及先验元素,就我们利用几何来处理问题的某些方面(例如弓的形状)而言。但它也涉及对经验的众多诉求。通过仔细的实验,我们确定只要保持相同的角度,就会产生相同的颜色,或者双折射与反射相结合,产生主弓,或者水的折射率与空气具有它所具有的特殊价值。我们对喷泉的普通体验最初暗示了一种将复杂现象分解为简单元素的方法。毫无疑问,经验也涉及笛卡尔的光理论所援引的物质理论。没有先验理由说明为什么必须恰好有三个元素,它们具有笛卡尔假定的属性。当与经院形式和品质相比时,对简单性和可理解性的先验考虑说明了这一理论。但是,如果该理论不能解释范围广泛的现象,那么这些考虑就不足以保证接受该理论,正如笛卡尔清楚地认为的那样。
如果我们自由地解释Regulae的概念,那么Discourse的规则与Regulae的规则非常相似。但Discourse 的一个显着特征是缺乏对直觉和演绎的任何明确讨论。这些概念的幽灵出现在第一条规则中,因为笛卡尔建议我们永远不要接受任何我们不知道是明显真实的东西,除了那些清晰明确地呈现在我们脑海中以至于我们没有理由怀疑他们。这不包括仅依赖可能的假设。但它没有明确提到直觉或演绎。它暗示了一个我们迄今为止没有考虑过的问题,因为到目前为止它似乎还没有出现在我们考虑过的著作中。
在他的整个工作中,笛卡尔显然是一个基础主义者,至少在最低意义上他认为我们的一些信念是基于我们拥有的其他信念,而有些则不是基于其他信念。我们可以称那些不基于他人基本信仰的人。我们的基本信仰为我们的信仰体系提供了基础;我们的衍生信念,上层建筑。我们的信仰体系就像一座有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建筑,如果基础不牢固,可能会倒塌,这一比喻在话语和沉思中很突出,但仅隐含在规则中,笛卡尔提出算术和几何是唯一真正的科学,但优于所有其他所谓的科学,因为它们的初始假设是确定性的,并且数学家从这些假设中小心翼翼地推导出可以清楚地看到从它们得出的结论。
但是,Regulae没有区分绝对确定和仅可能的标准。它假设数学比其他科学更确定,因为它关注的对象如此纯粹和简单,以至于不需要做出经验使之变得不确定的假设。在那一点上,笛卡尔认为要证明对数学假设的依赖是合理的,这就是全部。但是在《话语》(和《沉思录》)中,他关注的是他早期的作品没有考虑过的问题。这不是创造永恒真理的问题,而是一个不同的怀疑问题。
我们并非天生具有完全成熟的认知能力。相反,我们的能力会随着我们长大成人而逐渐发展。在他们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不加批判地接受了父母、老师和其他我们尊重其权威的人提出的许多建议。然后我们遗憾地了解到,这些并不是完全可靠的来源。我们以这种方式接受的命题看起来很明显。然而,它们缺乏坚实的基础,我们可能会误认为它们,即使它们看起来最明显。这种反思给了我们一个理由,不仅让我们怀疑我们从他人那里接受的具体命题和基于这些命题的一切,而且让我们怀疑我们的认知能力,我们辨别真假的基本能力,是否像我们认为的那样可靠是。
的话语不仅确定这个问题; 它为此提供了解决方案。在这项工作中,笛卡尔并不满足于仅仅说我们通过直觉获得的基本信念是不容置疑或显而易见的。他想表明,我们对某些命题的理解如此清晰明了,以至于没有理由怀疑它们,即使是对可能构成怀疑理由的宽泛概念也是如此。所以在论述的第四部分他开始了一项计划,即拒绝任何他可以“想象出最不怀疑”的东西。这就是所谓的怀疑方法。对于他认为是怀疑的理由,他非常宽容。他准备允许即使是“怀疑论者的最奢侈的假设”也为怀疑提供了一些基础。如果一个信念能够经受住那个宽容的考验,我们就不能合理地要求任何更确定的东西作为我们信念的基础。如果我们要怀疑,我们必须有一些怀疑的理由。但是,如果我们希望在我们怀疑的尝试中幸存下来的东西是绝对确定的,我们必须彻底了解这种尝试;我们必须允许即使是最不可能的可能性也被视为怀疑的理由。
如果笛卡尔没有明显地发现一些东西来抵制他的怀疑尝试,这似乎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探索:参与这种有条理的怀疑并因此在思考的他是存在的。因此,我们遇到了通常称为“笛卡尔的我思”的标签,该标签源自法语话语中出现的推理的拉丁语版本(“我思,ergo,总和”):“ Je pense, donc, je suis ” (“我思;因此,我存在”)。
虽然这个推论有一些非常令人信服的地方,但尚不清楚笛卡尔声称他最初的确定性究竟是什么。在《规则》中,他引用了“我认为”和“我存在”作为凭直觉肯定知道的真理。如果那是他们的状态,那么任何一个提议都可能是示威的合适基础。在《话语》中,他似乎是从他的思想推断他的存在,好像他可以确定自己的存在,因为他可以确定自己在思考——而且,确定思考,必须存在(亚当和坦纳利) VI。,第32页- 33)。这表明他对自己存在的肯定是以下论证的结论:
(1)想,就必须存在。
(2) 我认为。
(3) 所以,我存在。
这种关于我思的思考方式自然引发了笛卡尔如何确定这个论证的前提的问题。的话语并没有明确问这个问题,但它有什么看起来像一个答案来,只要第一个前提而言,在笛卡尔说,他看到的很清楚,(1)为真。尽管《话语》没有提供任何直觉理论,但这看起来像是诉诸直觉,当笛卡尔质疑简单数学真理的确定性时,我们可能认为其可靠性受到质疑。
的话语甚至不似乎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它涉及到第二个前提的确定性。但在笛卡尔于 1638 年写给亨利·雷内里的一封信中,答案似乎是,当我们在思考时,我们不能怀疑我们在思考(亚当和坦纳里二世,第 38 页)。这可能暗示以下论证(2)的确定性:
(4) 在思考的时候,不能怀疑思考。
(5) 我在想。
(6) 因此,我不能怀疑我在思考。
但是,尽管笛卡尔似乎经常接受(4),或与之等价的命题,但有时他似乎拒绝这样的主张。在《话语》的早些时候,他写道:“许多人自己并不知道他们相信什么;因为人们相信一件事的思维行为与人们知道自己相信它的行为不同,这种行为经常发生另一个”(Adam 和 Tannery VI,第 23 页)。此外,由命题 (4) 到 (6) 组成的论证,如果被用作证明 (2) 的确定性,则看起来无可救药地自问自答:它假定了它声称确定性的命题的真实性(和确定性)证明。所以话语的我思论证,尽管它的名气和广泛的吸引力,是有问题的。幸运的是,正如我们将在下面看到的,这个论点在沉思中采用了一种不同的、更有吸引力的形式。
第四部分的其余部分简要概述了笛卡尔将在《沉思录》中更全面、更准确地发展的论证. 找到了一个他知道是正确和确定的命题后,他暂时形成了一个一般规则:我们非常清楚和非常清楚地设想的任何东西都是真的。反思他作为怀疑者的天性,因此是不完美的,他问他如何能够获得对自己以外事物的想法。他想,他们中的大多数,他本可以自己创造出来的。但上帝的观念是个例外。一个不完美的人不能使自己有一个完美的人的想法。因此,上帝必定是他对上帝的看法的原因。因此,上帝必须存在。对于这个因果论证,他添加了本体论论证的一个版本:如果上帝是一个完美的存在,就像我们想象的那样,那么他就不会缺乏存在的完美。确立了上帝的存在,他接着争辩说,因为我们身上的一切真实和真实都来自一个完美的存在,所以他暂时采用的一般规则是正确的:我们所有清晰明确的想法都必须是真实的。甚至那些不清晰分明的想法也必须有一些事实基础。这种对笛卡尔形而上学的描述提出了最好在以下沉思集的讨论中探讨的问题。
论述的第五部分和第六部分主要关注笛卡尔的世界,他写道,“某些考虑”阻止他发表。他用其内容的概要来吸引我们,省略了对其哥白尼主义的任何明确提及,但强烈暗示教会对伽利略的谴责是他当时无法发表的原因。他没有提到教会或伽利略的名字,但他所说的话一定在知情读者心中留下了一点疑问:“我服从的人,对我的行为的权威不亚于我的理性对我的影响。思想已经否定了不久前由其他人发表的物理学观点”(Adam 和 Tannery VI,第 60 页)。笛卡尔没有说他是否接受这个意见,但他确实说,在当局谴责之前他没有注意到工作中的任何东西”
笛卡尔显然没有放弃在他有生之年出版《世界》的所有希望。他甚至暗示他有责任发表它:如果像他所想的那样,他正走在发展正确而全面的物理学的道路上,不仅要说明天体,还要说明这里的所有主要物体地球,潜在的好处将是巨大的。这样一门科学将使我们成为“自然的主人和拥有者”。它将提供希望,以发现新的方法来保持我们的健康和延长我们的生命。他认为实现这一目标的障碍只有两个:生命的短暂和缺乏观察。尽管他先验地提出了他的物理学基础(“......,我只考虑了创造世界的上帝”),他报告说,当他从最初的原因出发,通过从它们中推导出来的最初和最普通的结果,到更具体的事物时,他发现唯一的方法就是可以发现特定影响的原因是构建培根所说的关键实验。
笛卡尔的原理是如此普遍,以至于他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从中推断出效果。为了确定在产生效果的多种可能方式中,上帝选择了哪一种,他需要设置不同的理论会产生不同的可观察结果的情况。为此,他需要资金进行研究。Discourse 的第 6 部分是,除其他外,呼吁热心市民看到他工作的价值并希望帮助他。但是,《话语》及其文章的整个计划也旨在引起人们对他的计划的如此浓厚的兴趣,以至于教会感到有必要允许他在有生之年出版他的《世界》。否则,他将在死后发表。
论述的第五部分和第六部分中的其他问题比他们在这里所能得到的更值得讨论:笛卡尔关于血液循环的发现,他独立于威廉·哈维做出的,以及他对自然基本定律是必须的必然真理的肯定在上帝可能创造的任何世界中都可以观察到。在这里,我们必须限制自己注意他的挑衅性学说,即动物不过是机器。在世界的各个部分在与人类打交道时,笛卡尔试图证明上帝可以制造出外观和行为与人体一样的机器,仅使用笛卡尔物理学所允许的物质和遵循上帝本性的定律。笛卡尔旨在对许多不同的动物功能进行机械解释,事实上,人类与低等动物共有的所有功能。他不认为机制可以解释所有人类活动。有些,特别是语言的智能使用,只能通过嵌入机器的理性灵魂的存在来解释。笛卡尔认为,我们可以从他们的语言使用中确定,我们周围的人形身体居住着理性的灵魂。(他没有被其他思想的问题困扰。)但是非人类的动物,不表现智能的语言运用,缺乏理性的灵魂;它们不过是复杂的机器,甚至缺乏我们所拥有的那种感觉。
这一学说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其中大部分影响是笛卡尔不会欢迎的。有些人认为在人类和动物王国的其他部分之间划出如此明显的区别是荒谬的。一些人指责笛卡尔主义者对动物残忍,或者至少没有充分的理由不这样做。有些人认为笛卡尔关于低等动物的观点是正确的,但认为人类根本不同的观点是错误的。它们也不过是非常复杂的机器。
争议的开始(1637–1641)
在1637 年 6 月出版《话语》及其随笔之后,笛卡尔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回应对其作品的批评,并准备在这一时期结束时出版他的《沉思录》. 对 1637 年出版物的批评往往不是集中在形而上学或认识论上,而是集中在他对科学机械解释的承诺上:光、血液循环和动物行为。在这一时期的早期,他试图让耶稣会的朋友们放心,他的工作不包含危险的创新。他向 Vatier 吹嘘(Adam 和 Tannery I,第 564 页),人类的理性从未如此强烈地支持这种信仰,而且这种变质,“加尔文主义者批评说,普通哲学无法解释这一点,我的很容易解释。” 但是到了 1640 年,耶稣会牧师皮埃尔·布尔丹对他的光学的批评说服了笛卡尔,他必须“与耶稣会会士开战(亚当和制革厂三世,第 752 页)”。
到那时,笛卡尔已经开始修改他关于形而上学的“小论文”(未来的第一哲学沉思),并计划在公开之前在二十或三十位神学家之间私下流通,以便他可以从他们的批评中学习需要什么在出版前更正或添加(Adam 和 Tannery II,第 622 页)。笛卡尔告诉梅森,他的形而上学著作将包含“我物理学的所有基础”,但告诫他不要告诉人们“因为支持亚里士多德的人可能会更难批准他们。我希望读者能逐渐得到习惯了我的原则,并在他们注意到它们破坏了亚里士多德的原则之前认识到了它们的真实性”(1641 年 1 月 28 日;Adam 和 Tannery III,第 298 页)。
笛卡尔特别渴望得到索邦大学对他的工作的认可。这似乎不合常理,因为他在《讲道》中说,既然上帝赋予我们每个人一些辨别真假的能力,他感到有必要不满足于接受他人的意见(亚当和坦纳利六世,第 13 页)。 27)。想必这是我们都有的义务。但经验说服了他,他需要当局的支持,让人们仔细阅读他的作品,并从具有释放自己回复纠缠,恶意的批评(亚当和制革III,第184,237。- 238)。
当沉思集于 1641 年 8 月首次出现时,最初的计划已经改变。笛卡尔没有首先在二十或三十位神学家中传播他的作品以获得可能导致改变的反对意见,而是将大部分作品的初步传播委托给梅森,后者选择了少数批评家,而不是所有神学家。笛卡尔没有根据这种批评修改文本,而是在很大程度上保持文本不变,在正文之后发表他收到的反对意见和他的答复。每个评论家都可以看到前面的反对意见,并在撰写自己的意见时作出答复。
第一套反对意见的作者是一位名叫约翰·范·卡特 (Johannes Caterus) 的荷兰天主教神学家。人们普遍认为梅森本人撰写了部分或全部匿名的第二组和第六组反对意见。第三、第四和第五组反对意见分别由Thomas Hobbes、Antoine Arnauld和Pierre Gassendi撰写。这些是第一版中包含的唯一反对意见。当第二版于 1642 年出版时,布尔丹神父提出了另外一套反对意见,并附有笛卡尔愤怒的答复。笛卡尔不是一个乐于忍受傻瓜的人,他发现很容易相信他的批评者是傻瓜。有时他是对的。
第一哲学沉思 (1641)
第一版的扉页声称笛卡尔是在“有学者认可的情况下”出版的,并且在他的作品中,他将证明上帝的存在和灵魂的不朽。这些说法都不是真的。虽然他和梅森尝试过,但都没有得到索邦神学院的批准。虽然笛卡尔确实为上帝的存在提供了几个论据,但他甚至没有试图证明灵魂的不朽。这两个错误都在次年出版的第二版的扉页上得到了纠正。但令人费解的是,它们最初是制造出来的。有些人将他们归咎于梅森,后者通过媒体看到了这项工作。他应该是从致神学院的献词中草率地推断出笛卡尔打算证明灵魂不朽的。但是在 1640 年 12 月,笛卡尔警告梅森不要指望在宇宙中得到永生的证明。冥想。笛卡尔认为他最多能证明的是,心灵与身体是不同的,当身体死亡时,他不会死亡。由于上帝是全能的,他总是可以消灭思想(亚当和坦纳利三世,第 265 – 266 页)。第二版的扉页只声称证明了身心是真正不同的,并没有任何声称得到学者认可的说法。
《沉思录》是一部有多重议程的作品。没有合理的解释者怀疑笛卡尔想要确立第二版扉页上宣布的宗教结论。但是第一沉思强调了一个不同的目标:在科学中建立一些坚定而持久的东西。正是这个项目吸引了笛卡尔的大多数英语语言学生,并使《沉思录》成为现代大学中最常用的文本之一。该项目不仅仅涉及验证我们对清晰明确想法的依赖。正如笛卡尔在给梅森的一封信(1641 年 1 月 28 日)中所说的那样,他也想让人们习惯他的物理学基础并摧毁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
第一次沉思开始于回忆话语的计划:摆脱所有过去的信念。笛卡尔假设,如果一个信念在彻底怀疑它的尝试中幸存下来,并且在它被视为有效怀疑的基础上是宽容的,那么它就具有无可置疑的资格,并为重建我们的信念体系提供适当的基础。如果一个信念不容置疑的事实是使它成为一个新的信念体系的适当基础,那么这个不容置疑就不能仅仅是一个心理问题。但是关于我们可以相信什么和不可以相信什么的事实与确定什么是不容置疑的有关。我们不能随意怀疑一个信念。我们一定有什么理由为疑问。这个理由不需要足够可能使信念变得不可能。但是,如果在彻底寻找某种原因之后,我们甚至找不到一丝怀疑的理由,那么我们无法怀疑这个命题不仅仅是关于我们的心理事实。
我们该如何进行?如果我们不得不单独质疑我们的每一个信念,那么怀疑所有信念将是一项无止境的任务。幸运的是,我们的许多信念都是基于其他信念。如果我们动摇了根基,我们就会动摇其上的一切。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我们的信念都是基于对感官的信任。笛卡尔实际上在第一次沉思的早期就说过,他过去的所有信念都是如此。但是当弗兰斯·伯曼就此向他提问时,他解释说,在冥想中对我们说话的“我”是一个开始进行哲学思考的人,一个持有任何人可能持有的观点的人,如果他没有对他的信仰进行批判性反思的话。称这个虚构的人为“冥想者”。笛卡尔并不赞同冥想者表达的所有观点,正如对话的作者赞同他的人物表达的所有观点一样。在第一次禅修结束之前,反省会引导禅修者放弃这个经验主义的假设。但一开始,经验主义占主导地位。
禅修者简单地将感官欺骗的常见案例视为怀疑的基础,但驳回它们,因为它们仅支持对小物体或远处物体的怀疑,而不是对所有物质对象的更普遍的怀疑。他认为,更严重的是做梦的怀疑含义。每天晚上,当他入睡时,他会做梦。在这些梦中,他的经历与他清醒时最生动的经历一样生动。或者至少,如果他的梦和他最生动的清醒经历之间存在差异,那么在梦中是无法辨别的。直到后来,当他醒来时,他才意识到自己在做梦。因此,就他所知,他现在有可能在做梦,无论他目前的经历看起来多么令人信服。如果可以对任何感官体验,无论多么生动,都没有基于感官体验的信念是确定的。如果所有正当的信念都基于感觉经验,那么没有任何信念是确定的。
这似乎是禅修者在第一阶段的反省中得出的结论。但是冥想是禅修者心中的对话,是他怀疑的一面和他的教条的一面之间的对话。经过反思,禅修者想到,也许算术和几何学,这些处理最简单和最一般的对象并且很少关心它们的对象是否存在于自然界的科学,可能不会受到梦境论证的影响。感官体验是我们了解自然界的主要方式。但如果数学科学不需要自然界中实际存在的对象,它们就可能不依赖于感官经验。如果他们不这样做,他们就不会受到表明感官经验不可靠的论点的指责。此外,如此清晰的真理似乎不可能被怀疑是虚假的。
然后,冥想者反思他长期以来所持有的信念的含义:有一位上帝,他可以做所有事情,并且使他成为现在的样子。如果有这样的存在,他似乎可能创造了他(冥想者),不仅对他周围的一切都有欺骗性的感知(因此他似乎看到了地球、天空和其他延伸的物体,即使没有这样的东西)事物),但也对即使是最简单的数学真理也有错误的信念——所以很明显二加三等于五,尽管这个命题是错误的。当然,禅修者也相信神是至善的,这样的人不希望他被欺骗。但禅修者毕竟会犯错误。显然,如果禅修者是一位善良的上帝所创造的,那么有时允许他受骗也符合上帝的善良。让他老是受骗岂不符合神的良善吗?此外,放弃上帝创造冥想者的假设也无济于事。他的事业越不完美,他就越没有理由认为自己的认知能力没有缺陷。
禅修者对这些争论没有答案。他的结论是,可以对他以前的所有信仰提出合理的怀疑,并且他有强有力的(validas)和仔细考虑的(meditatas)理由来解释这些怀疑。理由之所以强大,不是因为它们的可能性,而是因为它们的范围,因为它们对各种信仰,无论是否基于感官,都产生了怀疑。禅修者坚持认为他以前的信念仍然很有可能,相信比否认更合理。稍后他会将基于欺骗上帝的可能性的怀疑描述为“轻微(tenuis)和......形而上学”。许多评论家问笛卡尔如何知道他的怀疑论点的前提是正确的。答案是他没有,也不需要,声称知道这一点。由于禅修者寻求绝对的确定性,对于合法怀疑理由的唯一认知要求是怀疑不是他有令人信服的理由拒绝的怀疑。
在第二次沉思中,笛卡尔决心将任何承认哪怕是最轻微怀疑的东西都视为虚假的东西,他声称找到了他的阿基米德点,一个抵制所有怀疑的命题,他可以在此基础上建立他修正后的信仰体系。他最初的确定是自我的存在。但是关于他存在的确定性的论证采用了与《话语》中不同的形式。著名的推论—— “我思故,我存在” ——没有出现。相反,我思段落的结尾是“这个命题,我是,我存在,只要我说出它或在我的脑海中想象它就必然是真的”(亚当和坦纳利七世,第 25 页)。
这种表述,再加上笛卡尔在第二组答复中没有任何明确的推论和一些晦涩的评论,导致一些读者认为笛卡尔声称“我存在”命题具有直觉确定性。但我们必须记住,在《话语与沉思》中,笛卡尔是为没有读过《规则》的读者而写的。在《话语》和《沉思录》中,他都没有将直觉作为其认识论的中心概念。此外,与Discourse 一样,但与Regulae不同的是,沉思对直觉知识的范式,数学中最简单的真理,提出了尚未解决的怀疑。
除了将自我的存在视为某种东西之外,还有另一种选择,如果完全知道,则必须通过直觉或通过直觉的推理来知道。当我想段落打开时,禅修者正在回顾他的处境。他拒绝了所有身体的存在,但也许有某种无形的存在,他无法怀疑。上帝,也许?但是上帝还没有资格成为无可置疑的存在。在这个阶段,冥想者认为他自己可能是他对上帝的想法的原因。他自己呢?他的存在是否与他的身体的存在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至于没有它他就无法存在?不。如果他确信某事(说没有尸体),那么他一定存在,无论物体是否存在。也许一个超级强大的骗子正在欺骗他一切(包括他自己的存在)。但如果骗子在欺骗他,那么他就存在。
这里的斜体字强调了两个类似我思的条件,每个条件都有一个前提假设冥想者可能会卷入(说服自己,被骗子欺骗)并因此肯定他的存在。禅修者不承诺任何一个前因。关键是,无论他接受什么怀疑论假设,无论他对自己的信念负责还是欺骗者负责,都源于他存在的假设。笛卡尔找到了一种方法来证明接受某事物作为第一原则是正当的,而不会招致对教条主义的合理指责:如果一个命题的真实性来自任何可以有效地被引用以对其产生怀疑的怀疑假设,那么就可以接受该命题作为确定而无需其他论证,具体而言,无需从某些先前的确定性中推断出来,也无需诉诸无误的直觉能力。
任何有效的怀疑理由都必须包含怀疑者的存在。尽管有效的怀疑只需要满足一个弱的认知要求(我们没有令人信服的理由拒绝它们),但它们还必须满足另一个条件:它们必须解释,至少在推测上,从事寻求真理的人如何能够误会了。但如果他们这样做,他们必须说“也许,但你可能会误会,因为上帝在欺骗你,或者你在做梦,或者你自己就是这种想法的源头,等等。” 怀疑论者,如果他是理性的,而不是教条的,怀疑我们的信念,他必须争辩说,为什么事情在我们看来是这样的,即使事情并不像它们看起来的那样。他一这样做,就承认我们在想,
笛卡尔在第二次沉思中解决下一个问题时使用了相同的程序:沉思者现在确定其存在的这个自我是什么?禅修者从他假设哲学初学者会拥有的信念开始,并询问其中哪些(如果有的话)可以从根本的怀疑中幸存下来。禅修者认为他是一个既有身体(有形状和位置的东西,占据空间以排除其他身体,感官可感知,并且可以被其他与之接触的身体移动的东西)和灵魂(a精细的物质,如空气或火,注入全身并负责营养、运动、感觉和思维)。
在假设某个超级强大的恶意存在正在欺骗他的假设下,这些前反思的信念中没有多少可以幸存下来。禅修者已经拒绝了身体存在的信念,直到它能够在更稳固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为止。因此,他确定存在的自我显然不是有形的东西,也不能从事需要身体存在的功能。营养和运动必须去。起初似乎感觉也必须消失,因为感觉显然以感觉器官的存在为前提。只剩下念头了。正如自我的存在来自于对其产生怀疑的任何假设,它的思想也是如此(微不足道)。如果笛卡尔确定无可置疑的第一原理的程序是合理的,他本可以采用“我认为” 作为第一原则,并从该原则证明“我存在”。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他有时会表现出这样做的原因。
说禅修者是一个有思想的人,就是把许多不同的活动归于他:他理解许多命题,肯定一些命题,否定另一些命题,并暂停对其他命题的判断。这一切都隐含在他怀疑的一面和他的教条的一面之间的对话中。仔细想想,即使是感觉也是他无法否认的事情。不具有主体,他可能不会有感觉器官,但他不能否认它有时看起来他好像他是通过他以为他身体的某些器官感知的东西。而这种看似纯粹是一种心理现象,不受怀疑的怀疑。怀疑论者在试图解释为什么我们对身体抱有毫无根据的信念时假设了这一点。
在第二次沉思即将结束时,笛卡尔沉迷于看似离题的事情。虽然禅修者还没有解决他对身体存在的怀疑,但他说他会屈服于他的自然倾向,相信他比他了解这个神秘的自我更清楚地了解身体(他可以想象和感知)他既无法想象,也无法感知)。所以他决定检查一个特定的物体,一块蜡,看看他在那个物体上清楚地知道什么。他描述了它的特性:大小、形状、颜色、硬度、温度、味道、香味等。然后他将蜡放在火边,并记录它在这些变化的环境中所经历的变化。它的所有敏感属性都发生了变化。冷的变成暖的;硬变软;等等。但是蜡,他说,(数字上)保持不变,尽管它发生了质的变化。没有人怀疑这一点。他的结论是,不应将蜡与任何变化的敏感特性等同起来。他在蜡中清晰地想象出来的东西,不过是一个延伸的东西,可以改变它的形状,可以改变一般的东西。
笛卡尔从这个实验中得出了许多结论。首先,蜡,以及一般的身体,不是通过感官或想象,而是仅通过头脑来了解的。蜡能够以比禅修者的感官或想像所涵盖的方式更多的方式改变。只有头脑才能抓住蜡。其次,心灵比身体更为人所知。每当禅修者根据感官证据判断蜡存在时,那些感受并不能确定蜡的存在。但是他们确实建立了判断蜡存在的思维存在的存在。
这里似乎是题外话,对于确定沉思的主要宣布的结论没有必要,但确实有助于笛卡尔暗中暗示他的物理学基础的未宣布的目的。正如第二次沉思的中间部分澄清了我们的灵魂或思想的预反射概念,削减了不必要的东西以暴露思想的本质属性,因此结束部分澄清了我们的预反射的身体概念。在蜡通道之后,我们知道不要认为物体的可感知特性对它们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对于任何物体来说,唯一必不可少的一阶属性是它的扩展性。我们也知道不要认为身体天生就可以通过感官感知。
蜡通道还有另一个不明显的目的。笛卡尔在《沉思录》中的方法的特点是他没有正式定义他的中心概念,而是让它们以非正式的方式出现。笛卡尔的核心概念之一是清晰明确的观念,他在第三次沉思的开头首次突出地提到了这一点,在那里他提出了他的真理标准:无论他清楚地感知到什么都是真实的。直到他写了他的《哲学原理》,他才定义了“清晰”和“独特”(即便如此,这些定义也不是很有帮助)。但是蜡像段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范例,说明获得清晰明确的想法是什么。当禅修者开始反思蜡时,他的观念是不完美和混乱的。在他仔细考虑蜡的成分并剔除不必要的东西后,他的想法就清晰了。
第三次冥想说明了获得清晰和独特想法的过程的另一种方式。当禅修者在第一次默想中介绍上帝的概念时,他通过列举他认为上帝具有的几个属性来解释该思想的内容,其中包括他创造了禅修者,他可以做任何事情,他是至高无上的很好,而且他是真理的来源。禅修者面临的问题是,他不确定所有这些属性是否统一为一个存在。也许他是由一个全能的人创造的,他不是万能的,而且远非真理的来源,而是一个骗子。
上帝的观念是第三次沉思中上帝存在的两个论点的核心。这些论点的核心是,对于冥想者拥有上帝观念的唯一可能解释是,上帝确实存在并且已经在冥想者中植入了一种自我观念,就像工匠可能在他的作品上留下自己的印记一样。但这个想法的内容究竟是什么?笛卡尔在第三次沉思中为这个问题提供了三个答案。前两个涉及神圣属性的列表:上帝是至高无上的、永恒的、无限的、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并且是除他之外的万物的创造者(亚当和坦纳利七世,第 40 页);上帝是一个无限的实体,独立,至高无上的智慧,至高无上的力量,创造了冥想者和其他一切存在的事物,如果还有其他问题(Adam 和 Tannery VII,第 45 页)。法语翻译1647 年出现的Meditations为这两个列表增加了不变性。
这些不同的列表有几个显着的特征:所有三个都包含上帝是创造者并且他是无所不能的想法。第三次沉思中的两个列表都省略了在第一次沉思中造成麻烦的属性,即上帝是至善的,是真理的源泉。第三沉思列表都包括无限,这个属性将在上帝存在的论证中发挥重要作用。但是没有两个列表是相同的。这突出了第三次沉思将提出解决方案的问题。我们不能通过列举上帝的属性来充分解释上帝观念的内容。我们可能知道从哪里开始:他是创造者并且是无所不能的。但我们不知道该停在哪里。如果上帝是绝对无限的,那么不仅他的个体属性本身是无限的,他一定有无数个。没有有限的头脑能够将它们全部列出。正如我们在第一次沉思中了解到的那样,可能对某些候选人存在分歧。如果上帝创造了冥想者并且是无所不能的,但冥想者会犯错误并且在其他方面不完美,那么上帝是至善的,是真理的源泉吗?
第三次沉思所提出的解决方案是,最好将上帝理解为一个至高无上的完美和无限的存在(亚当和坦纳利六世,第 46 页),这意味着他必须拥有所有的完美,而且只有完美。这个公式是各种属性列表的概括,每个属性都是完美的。这是总结这些列表的有用方法,因为它涵盖了可能被忽略的属性,无论是无意中还是由于编译列表的头脑的限制。但最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一个标准来决定什么应该在名单上,什么不应该。如果一个属性是完美的,它应该是;如果不是,就不应该。
有这么完美的存在吗?笛卡尔在第三次沉思中首先解决了这个问题,提出了两个论点,每个论点都从假设我们有所描述的那种上帝的想法开始。在第三组反对意见中,托马斯·霍布斯挑战了我们对上帝有概念的说法。但是笛卡尔回答说,霍布斯的挑战取决于将想法与图像混淆。既然上帝是无限的存在,我们当然可以没有上帝的形象。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无法了解他。“每当我用语言表达某事并理解我在说什么时,就可以肯定,从这一事实来看,我对语言所指的事物有一个想法”(Adam and Tannery VII, p. 160)。如果有神论者肯定而无神论者否认上帝的存在,并且如果他们都明白他们在说什么,那么他们都对上帝有概念。
但是,仅凭我们对上帝有一个观念这一事实,怎么能证明他的存在呢?在第三次沉思中,论证是因果关系。它们首先依赖于一般因果准则,即总有效率的原因中必须至少与结果中的真实性一样多(Adam 和 Tannery VII,第 40 页)。笛卡尔赞同古代哲学的一条公理,即事物不能从无中产生。以前不存在的石头现在不能开始存在,除非它是由“正式地或显着地”存在的东西产生的,无论石头里有什么。笛卡尔从未真正解释过所引用的限定是什么意思。很明显,他不认为原因需要与结果具有相同的属性。如果是这样,那么无形的上帝,将无法创建扩展对象。同样清楚的是,如果原因不具有相同的属性,那么它必须具有“至少同样完美”的属性。除非来自“至少与热一样完美的数量级”(Adam and Tannery VII, p. 40),否则先前不热的物体不可能有热。这种语言显然并不意味着原因需要有热量。但目前尚不清楚该语言对可能的原因有什么限制。这种语言显然并不意味着原因需要有热量。但目前尚不清楚该语言对可能的原因有什么限制。这种语言显然并不意味着原因需要有热量。但目前尚不清楚该语言对可能的原因有什么限制。
从这个普遍的因果格言中,禅修者推断出一个特别适用于观念的因果原则:观念的原因必须包含至少与观念包含客观现实一样多的形式现实。如果我们理解什么是形式现实,我们就会理解什么是客观现实,因为客观现实可以用形式现实来定义。客观现实是作为代表实体的思想的一种属性,它与其对象的形式现实相关。将其对象表示为具有非常高程度的形式现实的想法将比将其对象表示为具有较低程度的形式现实的想法具有更多的客观现实。说一个想法具有客观现实性并不是说它的对象存在。所有的想法都有一定程度的客观现实,即使有些想法有不存在的对象。同样,所有对象都具有某种程度的形式现实,即使有些对象并不存在。
笛卡尔的观点是,所有的思想都有一定的内容,其内容需要因果解释。在第一组回复中,他以一个拥有高度复杂设计的机器的想法的人为例说明了这一点。该人可能通过观察具有该设计的真实机器而获得了该机器的想法。但也许没有这样的机器。如果不是,我们必须为他对那个物体的概念寻找其他原因,也许是在他广泛的力学知识中。如果他对机器的想法既不是从观察过这样的机器也不是从他的力学知识中得出的,那么他可能是从见过这种机器或具有必要的力学知识的人那里得出的。但不管是什么原因,必须有一个足以产生那个结果的原因。上帝的想法,如同拥有上帝所应具备的所有完美的无限存在的想法比有限实体的想法具有更多的客观现实性。事实上,它具有一个想法可能拥有的尽可能多的客观现实,因为它的对象尽可能地完美。
剥离其本质,论证如下:1)每个想法必须有一个原因,该原因至少拥有与该想法代表其对象的形式现实一样多的形式现实。2)上帝的观念将其对象表示为具有最大可能的形式现实。3)因此,我们对上帝的观念的唯一可能原因是具有最大可能形式现实的存在(即,等于所有可能的完美)。4)因此,上帝的观念必须以上帝为原因。5) 因此,上帝存在。笛卡尔的读者普遍不接受这个论点,部分原因是所涉及的因果原则含糊不清,部分原因是笛卡尔似乎已经排除他自己使用这样的论点。
该论证诉诸于笛卡尔所说的由自然光可知的因果原则,自然光是一种认知能力,其解救能力在任何方面都不容怀疑。(亚当和制革厂七世,第 38 页)。作为众所周知的事情之一的例子,他提出了一个命题:“从我怀疑的事实来看,我是。” 但就在他开始争论之前,他说在他知道上帝是否存在并且可以是一个骗子之前,他无法确定任何事情(亚当和坦纳利七世,第 36 页)。而他似乎在那里将上帝欺骗的可能性作为怀疑的理由,不仅是简单的数学真理,还有“如果我认为我是某物,我就是某物”的命题——这个命题大概会被那自然光知道,它的释放是毋庸置疑的。看起来,为了证明自然光的可靠性,笛卡尔需要构建一个不欺骗上帝存在的证明。为了构建这个证明,他需要部署自然光已知的前提,在他确定自己的结论之前,他无法确定这些前提。推理看起来是循环的。因此,难度被称为笛卡尔圆。
在我们考虑第四次冥想之前,我们将没有材料来回应这一反对意见。但首先我们必须简要指出,笛卡尔在第三次沉思中提供了第二个因果论证,从亚当和制革厂 VII 的顶部开始,p。48. 这个论证的重点不是解释禅修者关于上帝的观念的存在,而是禅修者作为一个拥有这种观念的存在而存在。这个论点也没有说服很多读者,部分原因是它涉及到与第一个论点相同的一些概念上的困难。但它确实引入了对因果关系的另一个限制,这产生了有趣的后果。
在论证的某一点上,禅修者认为他作为一个拥有他所拥有的上帝观念的存在的存在的可能性可以通过说他一直存在来解释,就像他现在所做的那样。这似乎不是一个合理的假设,因为很少有人可能认为它们一直存在。但是笛卡尔拒绝它的理由很奇怪。他回答说,每个人的生活可以分成无数个部分,每个部分都完全独立于其他部分。从禅修者在某一刻存在的事实来看,并不意味着他会在下一刻存在。显然到那时他将不复存在,除非当时有某种原因再次创造了他。因此,禅修者需要一个因来支持他从一个时刻到下一个时刻的存在,就像他需要一个使他存在的原因一样,如果他不是一直存在的话。当然,那个原因必须是上帝。
这个立场的有趣之处在于假设,对于解释结果的原因,结果的存在必须从原因的存在逻辑上推导出来。全能者的意志可以满足这种因果关系的要求。全能概念的一部分是,如果一个全能的存在愿意某事,那么它所愿意的就必须发生。但是似乎没有有限的存在能够满足条件。对于任何假定的有限原因,它总是可能存在而不产生我们认为它具有的结果。这种对因果关系的限制看起来很快就会导致偶然主义的学说,即没有有限的存在永远是真正的原因,上帝是任何事情发生的唯一真正原因,明显的有限原因只是他愿意的事情发生的机会做。
在第三次沉思的结尾,笛卡尔将他最长的沉思中的大部分时间用于阐述上帝存在的两个复杂论证,快速论证上帝不可能是骗子。证明了其存在的上帝是至高无上的完美存在,拥有一切完美无缺。自然光表明,所有的欺骗都包含一些缺陷。所以上帝不可能是骗子。当然,有一个尴尬的事实,在第一次沉思中提到,上帝的创造物有时确实会犯错误。直到下一次沉思,笛卡尔才会试图将他的意识与他的信念调和,即一个极其完美的人创造了他。
在第四次沉思中,对这个困难的主要回应是对邪恶问题的标准方法的一种变体:尽管上帝创造了冥想者的本来面目,但上帝不对冥想者的错误负责,因为它们源于冥想者的误用上帝赋予他的自由意志。自由意志是伟大的,足以补偿禅修者的错误所涉及的任何邪恶。如果禅修者适当地运用他的自由意志,他就不会犯错。
在第三次沉思中,笛卡尔将他的思想分为三种:思想,虽然不是图像,但就像图像就其将对象表示为具有某些属性而言;意志或情绪,包括对一个对象的想法以及对它的某种情感态度(想要它、不喜欢它、害怕它等);和判断,这涉及对一个对象有一个想法,并肯定或否认关于该对象的某些事情。只有判断可以是真或假。禅修者最常犯的错误是判断他以外的事物是他的观念所代表的。当它们不是时,通常情况下,他就犯了错误。但错误,就像任何判断一样,总是涉及意志的行为,要么肯定某事,要么否认某事。禅修者自由地做出判断。如果他犯了错误,那是他的错,而不是上帝的错。
这里使用的自由概念需要一些检查。在一句话中,笛卡尔提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自由概念。这句话是这样写的:
意志或选择的自由……仅在于,我们可以做或不做某事(即肯定或否认,追求或逃避,同样的事情),或者更确切地说,仅在于,当理智向我们提出了肯定或否定、追求或回避的建议,我们是如此倾向于以至于我们不觉得我们被任何外力所决定。(Adam 和 Tannery VII,第 57 页;添加了重点)
这个令人费解的句子给翻译和解释带来了困难。但是笛卡尔的意思似乎是,第一个子句(在“或者说”之前)描述了我们可以获得自由的一种(不确定的)方式,而第二个子句(在“或者说”之后)描述了我们可以获得自由的另一种方式(不假设不确定性)。
笛卡尔的观点似乎是这样的:很多时候,当我们肯定某事时,我们可以否定它,而当我们否定它时,我们可以肯定它(或者既不肯定也不否定)。这在各种情况下都是正确的:我们可能没有任何证据;我们可能在各方面都有证据,但证据可能并不偏爱一种方式;或者该命题的证据可能比反对它的证据更重要,也许非常强烈,但没有定论。在所有这些情况下,我们将有权决定任何一种方式,并且在笛卡尔定义的第一条下是自由的。这通常被称为冷漠的自由,尽管该术语具有误导性的含义。这可能表明我们没有一种方式或另一种方式的证据,或者我们的一种方式的证据并不比另一种方式的证据更有力。正如笛卡尔设想的这种自由,这并不总是正确的。在我们对一个命题的证据有力但不确定的情况下,就像我们对物质对象存在的感觉证据一样,否认或中止判断将是困难的,但并非不可能。
但有时,笛卡尔认为,我们发现我们不能不做判断。在第二次禅修中,当禅修者在检查世界上是否有任何东西,并注意到他在检查这个事实时他存在,他不能不判断他所理解的如此清楚是真实的。他不知道有任何外力迫使他如此判断。相反,他的意志的极大倾向来自于他的智慧之光。他似乎越不冷漠,就越自由。这就是有时被称为自发性的自由,这一概念表明没有外部约束就足以获得自由。为了我们的自由,我们不必有能力以与我们不同的方式行事。
笛卡尔想要允许冷漠的自由和自发的自由。当我们没有清晰明确的想法时,我们就有了漠不关心的自由。我们可以用任何一种方式来判断。当我们确实有清晰明确的想法时,我们无法做出其他判断,但我们仍然是自发地判断,而不是受到任何强制。没有外部强制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判断没有外部因果关系。笛卡尔明确地承认,上帝可能正在处置冥想者内心深处的思想来判断他的行为方式。这不会减少他的自发自由,尽管这意味着他不再有漠不关心的自由。
一些批评家认为笛卡尔的判断理论非常不可信。本尼迪克特·德·斯宾诺莎 (Benedict de Spinoza) 认为,笛卡尔在他声称的某些情况下认为我们可能有漠不关心的自由时,他将判断与话语混为一谈。这是一两件事,说外部世界的,一个人的经历可能没有多梦的基础,又是另一回事居然相信它。第一个很容易;第二个很可能是不可能的。再一次,笛卡尔要求上帝为我们的错误免除责任的冷漠自由是否与他的教义相一致,即上帝在每时每刻都在不断地创造我们?不断创造的教义似乎让我们完全依赖上帝;冷漠的自由似乎使我们至少部分地独立于上帝。
一直以来,笛卡尔都在争论我们对某些观念有漠不关心的自由,但归根结底,他似乎并没有依靠这种自由来调和上帝的良善与错误的发生。在第四次沉思结束时,他承认上帝可以很容易地使沉思者在不失去自由的情况下永远不会犯错。上帝所要做的就是让禅修者清楚清楚地了解他将不得不做出判断的每一件事,或者在他心中植入一个坚定的决心,只对他清楚而清楚地感知到的事物做出判断。在第四沉思的最后几段中,笛卡尔对错误问题的解决似乎根本不依赖于自由意志,而是基于这样一种思想,尽管如果禅修者从不犯错,他可能会更好,有可能整个世界因为有犯错的人而变得更好。多样性是宇宙的调味品。
然而,第四沉思中的审判教义具有相当的系统重要性。怀疑的方法要求我们对任何我们最有理由怀疑的事物都暂缓判断,对我们没有清楚明白地感知的事物不表示同意。此外,它是有争议的原因笛卡尔的辩护取决于我们的能力从允诺的事情,我们不要做清楚而清楚地感知。如上所述,当笛卡尔在第三次沉思中论证上帝存在而不是骗子时,他经常将这些论证的假设证明为事物“通过自然光显现”。并且不清楚,根据第一次沉思的论点,在他首先确定上帝是否存在并且是一个骗子之前,他如何能够对那种或任何其他认知能力充满信心。
至少自 20 世纪中叶以来,评论家一直不愿指责笛卡尔公然循环。但对于他如何逃脱指控,目前还没有达成共识。这是一个尝试。笛卡尔认为,当我们关注它们时,我们清晰而独特的想法会迫使人们同意,这一点是没有争议的。当我们在一些一般性的标题下考虑数学的简单命题时,我们可能会怀疑它们,比如“对我来说最明显的事情”。但是当我们真正关注一个特定的简单数学命题时,我们实际上无法怀疑它。它迫使我们同意。笛卡尔认为,一些形而上学命题也是如此,例如“只要我认为我是某物,我就是某物”和“如果我现在存在,
第三次沉思中关于上帝存在和非欺骗的论证是由两种命题构成的。一种报告禅修者意识的内容,特别是他对上帝有一个想法的事实。这是与怀疑论者对话的前提,并且服从上面为“我存在”和“我认为”命题提供的辩护。另一种是一般命题,例如“原因必须至少具有与其结果一样多的真实性或完美性”,以及“欺骗是一种缺陷”。如果我们清楚清楚地感知这些事情,我们在关注它们时就不会怀疑它们。笛卡尔可能没有想到它们是不言而喻的,因为一旦我们理解了这些术语,它们就会得到同意。但是,如果它们没有得到同意,那么我们还没有清楚清楚地感知它们。我们在某些方面感到困惑,也许是因为那些似乎反驳这些原则的不太理解的经验。
假设我们能够完全依靠关于我们无法怀疑的意识内容的命题和我们清楚分明地感知的一般命题来构建上帝存在而不是骗子的论点,当我们参加时,我们也不会怀疑这些命题给他们。如果我们清楚而清楚地认识所有这些前提,并且同样清楚地看到它们与结论的联系,我们就不会怀疑结论。
怀疑论者现在可能会说:“我明白你不能怀疑上帝存在而不是骗子。但这只是关于你的事实。这并不意味着该命题不值得怀疑。也许你的创造者是一个无所不能的恶魔,而你的这种信念只是他的另一种诡计。”关于这里提供的解释,笛卡尔会说,一旦他有一个令人信服的论据来证明他是由一个不是上帝创造的上帝一个骗子,当我们同意我们实际上无法怀疑的想法时,仅仅假设恶魔可能在欺骗我们是不够的。对我们来说很明显,构成了一个有效的怀疑理由,因为我们没有令人信服的论据反对它。到第四次沉思结束时,我们确实有一个令人信服的论据反对它。因此,它不再构成有效的怀疑理由。怀疑理由的有效性视情况而定。在论证的一个阶段构成有效怀疑理由的东西,当我们没有令人信服的论据反对它时,当我们确实有这样的论证时,将不再有效。笛卡尔在他对第七组反对意见的答复中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Adam and Tannery VII, p. 473– 474)。
考虑一下我们在蒙田为雷蒙德·塞邦德的道歉中发现的Pyrrhonian怀疑论可能会有所帮助。皮浪主义者提倡蒙田所说的等价原则:对于支持一个命题的每一个论点,都有一个同样强烈的反对它的论据。蒙田关于论证强度的标准是心理说服力。当持有等价原则的人面对一个令人信服的论点时,他不能再仅仅通过假设一个全能的存在欺骗的可能性来对这个结论产生怀疑。他必须为相反的结论提出同样有力和令人信服的论据。如果没有这样的论证,笛卡尔就有权得出他的结论。
还有一个方面,第四禅结束时的情况与第三禅开始时的情况不同。现在我们对上帝有了清晰而清晰的认识。在第三次沉思的开始,我们只是将上帝设想为一个全能的创造者,他应该是至善的,是所有真理的源泉。但是我们没有看到这些属性之间有任何必要的联系,我们担心我们可能是由拥有这些属性中的一些而不是全部属性的人创造的。到第四次沉思结束时,我们明白上帝本质上是一个至高无上的完美存在,他拥有所有的完美,没有缺陷。一旦我们看到了这一点,我们就会发现全能骗子的假设是不连贯的。
在第五沉思中,笛卡尔的议程上有两个项目:考虑物质事物的本质和再次论证上帝的存在。他说,如果他要从怀疑中恢复过来,他最紧迫的任务是确定他是否可以对物质事物有任何确定性。在他决定这些东西是否真的存在之前,他需要考虑一下他对它们有哪些不同的想法。他在第二次沉思中为这种考虑准备了基础,在那里他将扩展确定为蜡中随着蜡变化而保持不变的一个一阶属性。在那里,他的注意力集中在一个特定的身体上。这里是关于他所谓的“连续量……或者这个量——或者更确切地说,被量化的事物——的扩展——长、广度和深度。”(Adam 和 Tannery VII,第 63 页)。因此,我们将几何空间(连续量)视为在三个维度上扩展的物质实体,其中特定的物体是部分,每个部分都拥有自己的自己的大小、形状和位置,并通过它们不同的运动与其他部分区别开来。(在这里,笛卡尔再次暗示了他的物理学的基本命题。)
当笛卡尔反思他的扩展对象的想法时,他意识到他有无数关于几何对象的想法,这些对象可能不存在于他的头脑之外的任何地方,但仍然具有确定的性质,“真实和不变的性质”,独立于他的头脑. 他可以证明这些形状的特性,即使他可能从未观察过他所展示的那种特性的任何形状。他可能观察到了三角形;他不太可能观察到千角形(千边多边形)。但是他可以确定它的属性是什么,即使没有观察到的千角形。每当他清楚地看到某些财产属于某事物真实不变的性质时,该财产确实属于该事物。他对上帝是一个极其完美的存在有一个清晰而清晰的认识。他明白,一个人要达到完美,就必须具备一切完美,而存在就是完美。因此,他推断上帝必须拥有完美的存在。
这个版本的本体论论证依赖于柏拉图的数学哲学,皮埃尔·加森迪在第五组反对意见中批评了这一点。加森迪首先抱怨说,在他看来,除了上帝之外,很难坚持存在真实和不变的本性。他想象笛卡尔的回答是,他只是在说学校里说的话,事物的本质是永恒的,关于它们可以有真实的命题。但是加森迪不明白某物的本质是如何存在的——他的例子是人——如果没有那种东西。有一次他似乎愿意承认,即使没有人存在,“人是动物”也可能是真的。但他说,这句话只有在有条件地理解时才是正确的:“如果某物是人,那它就是动物。” 他对这个条件进行了分析,该条件使其真理显然需要某些人的存在:
当人被说成具有这样一种性质,以至于他不是动物就不能存在时,不能因此而想象这种性质是某种东西或在智力之外的某处。意思只是一个东西要成为一个人,他必须像其他那些我们给同一个名字的东西一样,人,因为它们相互相似。(亚当和制革厂 VII,第 320 页)
加森迪还质疑存在是否是完美的:“存在在上帝或其他任何事物中都不是完美的;没有完美就不可能存在完美。......不存在的东西没有完美或不完美。......如果一个事物缺乏存在,我们不会说它不完美……而是说它根本就没有”(Adam 和 Tannery VII,第 323 页)。尽管 Gassendi 专注于存在可能是一种完美的想法,但他的推理似乎排除了它是任何类型的财产。他不是将存在视为事物的谓词,而是将其视为任何谓词的前提。
当笛卡尔回答时,他对加森迪想把存在归入什么范畴感到困惑。在他看来,存在类似于全能,一种可以被事物谓词的东西,因此是一种属性。但随后他拒绝了 Gassendi 对基本谓词的条件分析。Gassendi 的例子,人,是“辩证法家的普遍者”之一,即经院哲学家。笛卡尔更喜欢关注我们清楚明白的本质,比如几何图形。我们不能像经院哲学家和加森迪那样理解后者的本质,因为它们基于从概念实例的经验中抽象出来的概念,因为我们没有实例可以体验。这不仅适用于像辣椒这样陌生的人物,但也适用于像三角形这样明显常见的图形。问题在于,根据我们的经验,没有任何东西严格满足三角形的定义,除其他外,它要求它由直线组成。当仔细检查时,我们体验到的线条并不是完全笔直的。但是我们可以将我们体验到的图形识别为理想几何图形的近似值,因为我们对理想图形的想法来自另一个来源。
笛卡尔对加森迪对本质谓词的分析的反对可能比他反对我们的概念是从经验中抽象形成的经院理论更深刻。他似乎很可能会拒绝对基本谓词进行任何有条件的分析,即使它不是用抽象主义的术语来阐明的。加森迪抱怨说,笛卡尔所谈论的本质,除了上帝之外,不可能具有永恒不变的本质。笛卡尔回答说,他并没有声称事物的本质独立于上帝而存在。他认为它们取决于上帝的旨意,并且认为它们是不可变的,只是因为上帝的旨意是不可变的。虽然笛卡尔没有明确援引他的关于在沉思集的主体中创造永恒真理的学说本身——(他可能在第三次沉思中预设了这一点),他确实在他对反对意见的答复中明确表达了这一点。(它在第六组答复中再次出现。)对可能导致笛卡尔提出永恒真理创造学说的原因的反思也可能表明他拒绝加森迪对基本谓词的条件分析的原因。
经院哲学家在思考本质谓词时面临的一个问题是,根据普遍命题的正统理论,它们具有存在意义。“所有的人都是动物”意味着有男人。但是,如果“所有人都是动物”是一个必然的真理,那么它的蕴涵也是如此。然而,“有男人”应该是一个偶然的真理,在上帝的旨意创造时成为现实。笛卡尔可能已经将永恒真理与国王在其王国中制定的法律进行比较,因为国王的法律的有效性不取决于违反这些法律的人的存在,而仅取决于其来源的权威性。国王禁止决斗并不取决于是否有决斗者。笛卡尔可能认为,对基本谓词的条件分析避免了一个问题,结果却引发了另一个同样困难的问题。在没有人的假设下,“如果有什么是人,那它就是动物”是一个条件,其前提是错误的。如果这是一个物质条件,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也是如此,正如条件“如果有什么是人,它就是一株植物”。如果是模态条件,则不清楚这些条件的真值条件是什么(如果有的话)。
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提出了一个同样严重的问题,他认为笛卡尔需要用上帝的概念是一致的证明来补充他的本体论论证。可以说,这就是笛卡尔在第四次沉思中以有限的方式试图做的。那次沉思试图解决自第一次沉思以来就威胁到他对上帝的概念的矛盾:上帝是一个完美的人,但他被认为创造了一个非常不完美的人。但强调人类自由是该问题的解决方案,即使这不是笛卡尔的最终解决方案,也只是提出了人类自由是否与上帝的全能相容的问题,这是笛卡尔在其《哲学原理》中要解决的问题。
在第六禅定中,议程上有两个宣布的项目:建立身体的存在和证明身心是不同的。解决后一个问题的第一步是认识到(1):
(1)凡是我清楚明白的,神都可以按我的理解来造。
这里的想法似乎是,如果我清楚明白地理解某事,它就必须没有矛盾,而且无所不能的上帝可以创造任何不涉及矛盾的东西。从(1)得出(2):
(2) 如果我清楚明白地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有思想、没有延伸的东西,那么上帝就可以把我创造成一个有思想、没有延伸的东西。
类似地,(3)也从(1)推导出来:
(3) 如果我清楚明白地把身体想象成一个延伸的、不思考的东西,上帝就可以把它创造成一个延伸的、不思考的东西。
在第二次沉思中,笛卡尔的沉思者在他的推理中达到了满足(2)和(3)的前提的状态。他对蜡是一种延伸的东西有着清晰而清晰的认识,他没有将任何思想归于它,并且他对自己是一个会思考的东西有着清晰而明确的认识,他没有将任何有形的东西归于它。所以他推断(4)和(5):
(4) 上帝可以将我创造为一个有思想的东西,与我或任何其他身体分开。
(5) 上帝可以创造我或任何其他身体作为一个扩展的东西,除了我或任何其他有思想的东西。
为了表明两种事物确实是不同的,将它们创造为单独的实体需要什么力量并不重要。根据真正区别的定义,如果两个事物是实体,则它们是真正不同的,并且每个事物都可能在没有另一个事物的情况下存在。所以这足以证明:
(6) 我和我的身体是真正不同的物质。
这个论点有什么问题并不明显,尽管它肯定不乏批评者。
在第四组反对意见中,Antoine Arnauld提出了以下反例。一个人可能清楚而清楚地感觉到内接在半圆内的三角形是直角的,但不知道勾股定理,根据该定理,直角三角形斜边上的平方必须等于其上的平方和另外两侧。因此,他可能会怀疑或否认内接于半圆的特定三角形具有勾股定理。从笛卡尔的第一个假设 (1) 中,他可以推断出 (2 ′ ):
(2 ′ ) 如果我清楚明确地将内接于半圆的三角形设想为直角,但怀疑或否认该三角形具有勾股定理,那么上帝可以创造一个内接于半圆的三角形不具有该性质。
这个条件的前提很可能是正确的,似乎,但随之而来的将一种他无法拥有的力量归于上帝,即使我们接受笛卡尔关于创造永恒真理的学说。即使上帝可以为三角形创造一个不同的性质,他的意志的不变性意味着他现在不能创造一个具有不同性质的三角形(亚当和坦纳里五世,第 160 页)。笛卡尔详细地回答了阿诺德的反对意见,但似乎从来没有达到这一点。他应该说些什么来为自己辩护并不明显。
尽管笛卡尔将身心视为能够彼此分开存在的物质,但他也急于坚持自己的身体与身体非常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就像是混合在一起”(Adam and Tannery VII, p. 100)。 81),这样他就可以用它来创作一件事。他的身体感觉教会了他这一点:当身体受损时他会感到疼痛,需要食物时会感到饥饿,需要喝水时会感到口渴。当类似的事情发生在其他身体上时,他不会感觉到这些感觉。所以,他说,大自然教会他,他不仅仅是在他的身体里,就像一个水手在他的船上一样。因此,他拒绝了中世纪认为柏拉图过度二元论的东西。身体感觉只不过是由身心结合而产生的混乱的思维方式。尚不清楚这种身心结合的学说是否与身心不同的学说相容。这成为了《宣言》发表后的一个主要争论话题。冥想,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
笛卡尔试图证明物体存在的尝试引起的争论与其说是驳回,不如说是驳斥。他说,上帝给了他很大的倾向,相信他的感觉是由物质事物引起的,并且没有能力识别它们的任何替代来源。所以笛卡尔不明白,如果上帝的感觉是由某种无形的东西引起的,他怎么能免除欺骗者的罪名。一定有肉体的东西。它们可能没有他通过感觉所掌握的所有属性,因为这些属性中有很多是模糊和混乱的。但它们必须具有他清楚明白的所有性质,即纯数学学科的所有性质。
真的很难想象一个完美的上帝怎么会允许如此巨大的妄想。但是笛卡尔在这里削弱了判断上帝是骗子的条件。在第四次沉思中,如果我们有无法避免的错误信念,上帝就会是一个骗子。现在,即使我们有我们可以帮助拥有的错误信念,上帝也是一个骗子,只要我们非常倾向于相信它们并且无法判断它们是错误的。也许从这个论点得出的正确结论是,我们对物质对象的信念不可能是错误的。当我们处理我们可以的信念时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持有错误的信仰,我们可能需要先了解一些关于上帝旨意的信息,然后才能决定他是否会成为骗子。笛卡尔不认为我们可以知道上帝的目的是什么。但是,这个论点没有得到多少支持的主要原因可能是,我们似乎不必接受这个复杂的有神论论点才能将物体的存在视为确定的。
我们应该注意到笛卡尔在第六次沉思中得出的一个重要的否定结论:即使我们是由一位不欺骗的上帝创造的,我们也没有理由相信我们通过感官感知的事物具有我们倾向于归因的所有属性他们。我们混淆和模糊概念的属性——我们认为热物体的热量,我们认为绿色物体的颜色,以及后来哲学家所说的“事物的次要性质” ——这些属性,就我们认为它们是外部对象的属性而言,不必与我们对它们的想法有任何相似之处。事物本身必定有区别,热的和冷的,红的和绿的。但是,只要外部物体的差异与我们感觉的差异之间存在系统相关性,我们就不必假设物体本身有任何类似于颜色或热量的东西。这是笛卡尔的物理学的基本原理之一,他滑入了沉思。
持续的争论(1641–1644)
甚至在1641 年 8 月《沉思录》出版之前,笛卡尔就已经开始着手他的下一部主要著作《哲学原理》(1644 年),他有时在信件中将其称为“哲学概要”或“哲学”。或作为他的“物理学”。他的目标是以论文的形式结合形而上学、物理学和生物学来制作他的哲学的“完整教科书”,“在那里,我将不加赘言,只提出我的所有结论,并附上从中得出的真实前提。我推导出它们”(Adam 和 Tannery III,第 233 页)。不会有任何错误的开始给冥想他们的辩证性格。当他第一次开始计划这项工作时,他想出版一本经院哲学的标准教科书,他会对此发表评论。为此,他选择了圣保罗的Summa philosophiae 的Eustachius ,但在 Eustachius 于 1640 年 12 月去世后放弃了该项目的这一方面。以一种逃避谴责的方式呈现他的宇宙观。
当第二版沉思出现1642年5月,它补充说,不仅父亲布尔丹的反对和笛卡尔的答复,但也从笛卡尔到父亲杰克斯·迪内,在拉佛罗里达州的一位老师的一封信èche,现在是法国耶稣会的负责人,抱怨布尔丹对他的待遇。笛卡尔有理由对布尔丹感到不安:他在解释笛卡尔的观点时啰嗦、讽刺和冷漠。笛卡尔说他表现出了砖匠的敏锐度,而不是耶稣会牧师。他写的拉丁文很烂。尽管笛卡尔似乎对耶稣会的一些成员有真挚的感情,并尊重社会在学校提供的教育质量,但他很容易在其成员的行为中看到阴谋。他担心布尔丹的批评不是一位耶稣会牧师的意见,而是代表了耶稣会士的共识。他敦促迪内亲自阅读《沉思录》——或者,如果他没有时间这样做,则将任务分配给比 Bourdin 更能干的社会成员——并让他知道他们是否在他的项目中发现了问题。DINET委派任务父西安娜·查尔,以前在拉FL校长è车,后来DINET的继任者,耶稣会士在法国,谁是写信给笛卡尔对他作品的头。Charlet 似乎最终向笛卡尔和他的作品展示了他个人的善意,但让他不确定整个社会的态度。
笛卡尔还在给迪内特的信中描述了他在乌得勒支大学卷入的一场争论。1641 年,他的追随者、大学医学教授 Henricus Regius 在那里进行了一场争论,他在那里提出了他的笛卡尔自然哲学版本,比笛卡尔认为的更明智。雷吉乌斯说,心灵和身体的结合是偶然的,而不是实体的,并且也否认实体形式的存在,那些在经院自然哲学中应该使它们成为事物的形式并解释事物的形式方面他们的特征行为。对于这些职位,Regius 遭到了大学校长 Gisbert Voetius 的攻击,他借此机会也向笛卡尔的方向投掷了一些倒钩。
雷吉乌斯觉得他需要公开回答,笛卡尔建议他该说什么。尽管笛卡尔认为雷吉乌斯的意思是可以接受的,当他宣布灵魂和身体的结合是偶然的——也就是说,思想和身体确实彼此不同,每个人都可以在没有另一个的情况下存在——他警告雷吉乌斯,经院学者会对这种语言有不同的解释,最好的办法是声称他们对经院术语一无所知,并说他们之间的分歧只是口头上的。关于实体形式,笛卡尔认为雷吉乌斯应该说他不想绝对拒绝它们,他的意思只是他的科学解释不需要引用它们。说火具有火的形式并不能帮助我们理解它燃烧木材的能力。这是笛卡尔所采取的立场,让他的读者得出结论,如果实体形式在解释上毫无用处,就没有理由假设它们。
当雷吉乌斯公布他的答复时,他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大学谴责新哲学并禁止雷吉乌斯教授他关于身体问题的课程。“乌得勒支大学是世界上第一所允许其教授教授笛卡尔主义的大学,也是第一所禁止其教学的大学”(Verbeek 1992,第 19 页)。当笛卡尔在给迪内神父的信中批评 Voetius 时,Voetius 的回应是安排格罗宁根大学的教授和他的门徒 Martin Schoock 写一本书,其中指责笛卡尔无神论和养育许多私生子。(事实上,笛卡尔确实有一个私生子,一个他非常喜欢的女儿,但她于 1640 年去世,享年五岁。)乌得勒支事件的完整故事——最终涉及诽谤诉讼、伪证指控以及禁止对笛卡尔进行任何讨论,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在这里说起来太复杂了(更多细节,请参见 Verbeek 1992)。
哲学原理(1644)
《原理》是笛卡尔最系统的著作,也是他的同时代人为了明确阐述他的哲学而去的著作。它由四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涉及形而上学和认识论,第二部分涉及物理学的一般原理,第三部分涉及天体现象,第四部分涉及地球现象。由于笛卡尔本人更喜欢在《沉思录》中阐述他的形而上学和认识论,而不是他在《原理》第一部分中给出的阐述,而且由于占主导地位的科学以现代标准来看是原始的,因此笛卡尔最近的学生都忽略了该原则. 在这里,我们必须限制自己只注意到它增加了我们从对笛卡尔其他作品的调查中了解到的许多东西中的一小部分。
增加的部分是笛卡尔在 1647 年法文翻译的序言中使用的一个比喻:“整个哲学就像一棵树,根是形而上学,树干是物理学,枝干是所有其他科学,它减少三门主要科学,医学、力学和道德”(亚当和制革厂 IX-B,第 14 页)。这段话说明了笛卡尔关于我们现在认为是完全独立的学科之间密切联系的概念,他在形而上学中建立科学的雄心,以及他希望他的基础工作能够产生实际后果的希望。特别有趣的是他从形而上学和物理学中导出道德哲学的野心。当我们谈到他的最后一部主要作品《灵魂的激情》时,我们将看到这导致了什么。
《原则》提出的一个微妙问题是宇宙的范围问题。哥白尼并没有宣称世界是无限的,但后来的哥白尼主义者,如乔尔丹诺·布鲁诺(Giordano Bruno)却做到了。虽然我们不知道教会在 1600 年处决布鲁诺的具体理由,但似乎这就是其中之一。由于笛卡尔将物质与(欧几里得)空间等同起来,因此他似乎也将致力于物理宇宙的无限性。但在原则(PT I,秒26。- 27),他说他不是。他只为上帝保留了“无限”一词,并指定了他无法发现任何限制的事物——例如世界的扩展和物质的可分性——无限期。然而,后来在《原则》(第 II 部分,第 21 节)中,他从否认世界范围有任何限制的知识转变为肯定世界范围没有限制的知识。当他后来开始发展他的道德哲学时,他将以下命题列为对我们最有用的真理之一:我们必须提防假设上帝创造的世界的范围是有限的(原则,第 III 部分,第 1 节)。笛卡尔认为,对上帝创造之浩瀚的欣赏将有助于我们将自己与这个世界的事物分离(亚当和坦纳里四世,第 292 页)。
另一种神学上敏感的问题,笛卡尔在第1部分处理的是协调人的自由与上帝的无所不能的问题(秒37。- 41)。笛卡尔在这里的自由概念似乎比沉思中的更加一心一意地不确定. 如果我们的行为值得称赞,我们必须以某种特殊的方式成为这些行为的作者,而不是我们的创造者决定这样做。否则我们一定能够做到。在许多情况下,我们有权同意或不同意,这一点与任何第一原则一样明显,尽管这不是天生的知识,而是我们从自身经历中学到的东西。另一方面,现在我们认识了上帝,我们看到他的力量是如此巨大,以至于认为我们可以做他没有预定的事情是不敬虔的。
最近关于使人的自由与上帝的属性相协调的问题的讨论往往集中在表明人的自由与上帝的预知是一致的。笛卡尔更担心表明它与上帝的全能一致。或许笛卡尔认为,他将上帝的意志与他的智力相结合,排除了他可能在没有预定的情况下预先知道的可能性。无论如何,笛卡尔提出的解决方案是我们应该同时保持我们的自由和上帝的预定,即使我们看不出它们如何兼容。上帝的力量是无限的;我们的智力是有限的。所以我们不应该期望了解它们如何兼容,我们不能仅仅因为我们的理解有缺陷而放弃两个这样的某些真理。
在原则的第二部分,笛卡尔为哥白尼主义的一个版本奠定了基础,该版本应该避免地球移动的谴责主张。在第 13 节和第 24 节中,当我们说一个物体移动时,他对我们通常的意思给出了一个相对论的解释:它改变了它的位置,这被定义为它相对于其他静止物体的位置。对于某物是否在移动的问题,我们将得到不同的答案,这取决于我们将哪些其他物体作为我们的参考系。假设一个人坐在一艘沿着河流驶向大海的船的船尾。如果我们考虑到他与他所坐的那部分船的恒定关系,我们就说他处于休息状态。如果我们考虑他与海岸的关系,我们就说他在移动,因为他不断地从某些部分移向其他部分。——我们的参照系现在是我们认为静止的天空中的某些物体。但是如果我们认为宇宙中任何地方都没有这种静止的点,我们就会得出结论,没有什么东西是永久的,除非它是由我们的思想决定的。在第二部分第 13 节中,笛卡尔预示了一个论证,他说,这使得宇宙中可能不存在真正的固定点。我们在第三部分第 29 节中得到了这个论点,他在那里争辩说,如果我们按照常规用法,没有理由说静止的是恒星而不是地球。
笛卡尔似乎拒绝普通用法。在第 2 部分第 25 节中,他说如果我们想“根据事物的真相”来理解运动,我们应该将其定义为“物质的一部分或一个物体的转移,从那些立即接触它的尸体,被认为是静止的,到其他尸体的附近”(强调)。因此,他将紧邻周围的天体视为一个特权参考系。根据这个定义,地球严格来说是静止的,尽管公认的感觉是它正在绕太阳运动。在笛卡尔的在宇宙学中,它相对于它周围的流体物质是静止的,它围绕着太阳旋转,就像一艘既不受风驱动也不受锚阻碍的船可能相对于它周围的水是静止的,虽然它被潮汐不知不觉地带到了海里(第 III 部分,第 26 - 28 节)。当然,正如笛卡尔所指出的,对所有其他行星也可以这样说。
笛卡尔学者经常怀疑笛卡尔采用这种严格的运动定义,仅仅是因为他可以声称在他的宇宙学中地球是不动的,从而允许他采用基本上哥白尼的天文学,而不会遭受伽利略的命运。笛卡尔预计,他对地球运动的否认可能会被认为“只是口头上的”,目的是避免受到谴责。但是他说仔细阅读他的作品应该可以消除这种怀疑(Adam and Tannery V, p. 550)。无论如何,可以说他有其哲学内在的严肃理由,想要以一种能够摆脱他在运动的普通概念中看到的相对主义的方式来定义运动。运动应该在他的机械物理学中做大量工作。正如他在原则中所说,“物质的所有多样性,其形式的所有多样性,都取决于运动”(第 II 部分,第 23 节)。为了对运动进行这种解释,他需要它是真正存在于身体中的某种东西,而不是存在于或不存在于身体中的东西,这取决于你如何看待它们。但他对问题的解决方案是非常成问题的,不仅因为它最终没有保护他免受教会的谴责。(有关这个复杂问题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Garber 1992,第 6 章。)
我们不能离开对这些原则的过于简短的讨论,而不会注意到笛卡尔最后评论了他认为他的科学理论所具有的认识论地位。他声称他们至少在道德上是确定的,也就是说,足够确定对它们采取行动是合理的(或者对它们采取行动可能是不合理的),即使它们不是绝对或形而上学的确定(第 IV 部分,第 205 节)。他的原理解释了如此多的现象,以至于它们几乎不可能是错误的。他认为,他的一些原则是绝对确定的,因为它们基于他的确定性,即上帝是至善的,不是骗子(第 IV 篇,第 206 节)。他提到了数学论证、物质事物的存在以及“关于物质事物的所有明显推理”。他显然希望他的读者能够发现他的更多形而上学结论。
皇家崇拜者,持续的冲突(1644–1648)
笛卡尔将他的哲学原理献给了腓特烈五世(前任选帝侯帕拉丁和波西米亚国王)和伊丽莎白·斯图亚特(英格兰查理一世的妹妹)的女儿伊丽莎白公主。1643 年,笛卡尔得知流亡海牙的公主阅读了他的《沉思录》后,他们开始通信。她向他提出了关于身心关系的尖锐问题,得到了一些令人惊讶的答案。后来他们的通信转向伦理和心理学问题,这促使笛卡尔写下他的最后一部主要著作《灵魂的激情》(1649),也献给她。尽管在他们的通信中普遍存在的奢侈的相互奉承可能仅仅是礼貌的礼节,但读者有时会怀疑笛卡尔是否对这个悲伤、可爱、聪明的年轻女子怀有感情,这可能会导致浪漫,如果没有年龄差异、社会地位和宗教使这成为不可能。无论如何,她证明了她是一个激励学生。
Elisabeth 通过提出一个问题开始了他们的通信,这个问题在笛卡尔主义的后续发展中成为核心:在自愿运动中,作为一个非扩展的东西,心灵如何能够导致它的身体,一个扩展的东西,移动(亚当和坦纳里三世,第 661 页)?她关于运动的可理解因果关系的范式——我们可能也认为笛卡尔的范式——涉及一个物体对另一个物体的影响,原因将它的一些运动传递给开始运动的物体。影响需要接触,这需要因果关系的延伸。一个非扩展的事物不能对一个扩展的事物产生影响。
笛卡尔回答说,解释心灵移动身体的力量是它与身体的结合(亚当和坦纳里三世,第 664 页)。身心合一的概念是一种原始的概念,就像广延和思想一样,无法用任何更基本的东西来解释。但笛卡尔认为,当我们归因于所谓的“真实品质”时,我们就证明了我们拥有这个概念,比如重量,一种将物体移向地球中心的力。尽管我们不知道重量,除了作为一种具有这种效果的力之外,我们认为它是移动一个物体并不困难,即使我们不认为它是通过实际接触另一个表面来实现的. 我们发现这很容易受孕,因为我们在自己身上体验到一种移动身体的力量,我们推断身体具有具有类似力量的品质。我们称这些品质为“真实的”,这意味着我们认为它们与拥有它们的身体完全不同,因此是一种实体。(事实上,正如笛卡尔在别处解释的那样,我们认为它们是一种精神实质,因为我们将目标导向的行为归因于它们。)
Elisabeth 对这种解释不满意,他指出,真正的品质是笛卡尔物理学旨在取代的经院自然哲学中声名狼藉的部分(亚当和坦纳里三世,第 684 页)。笛卡尔承诺对诸如重物体坠落到地球这样的现象给出适当的机械解释,这样就没有必要用神秘的品质来解释心灵移动身体的力量,这种力量只能通过它们的效果来了解。由于伊丽莎白并不真正了解重量,因此她无法利用所谓的因果力量来帮助她了解灵魂如何作用于身体。她承认,对她来说,给予灵魂扩展比假设一个非物质存在有能力移动并被一个物质所感动要容易得多。在他的答复中(Adam 和 Tannery III,第 694 页),笛卡尔允许她这样做:将灵魂视为扩展的存在!将灵魂视为延伸就是将其与身体结合在一起。Elisabeth 对这个回答也不满意,这似乎与说我们有一个清晰明确的思想是一致的,即思想是一种思考的、非扩展的实体。但在这个问题上,她没有从笛卡尔那里得到更多信息。
后来他们的通信转向伦理问题,笛卡尔建议他们讨论塞内卡的“De Vita Beata”(论幸福生活)。伊丽莎白作为流放公主的生活并不幸福。笛卡尔希望阅读塞内卡能帮助她克服抑郁症。显然,当他提出这个建议时,他没有读过塞内卡,或者最近没有读过他。当他这样做时,他没有发现那里有什么用处。但是,当他为实现幸福而提出自己的建议时,它们具有明显的斯多葛派风格:我们应该用理性而不带激情地考虑所有完美的价值,无论是身体还是灵魂,以便我们始终可以选择更好的。我们应该培养坚定而持续的决心,在不为我们的激情所转移的情况下,尽可能地执行理性的建议。美德在于坚持这个决心,而笛卡尔认为美德是通往知足的道路。但不久之后,他决定他需要更详细地检查这些激情,以便他能够定义它们。这导致了他的初稿灵魂的激情,写于 1645 年至1646 年的冬天。
虽然这些积极的发展正在发生,但与 Voetius 的争议仍在继续并蔓延到莱顿大学,在那里,该大学史泰登学院院长雅各布·雷维乌斯攻击了笛卡尔,而雷维乌斯在学院的副院长阿德里安·希勒布尔德为他辩护。这一次的主要问题与其说是笛卡尔对经院哲学中的关键思想的拒绝,不如说是他自己哲学的实证学说:
怀疑的方法是否会导致怀疑——考虑到笛卡尔在超越我思时所面临的问题,这是一个合理的担忧笛卡尔是否犯了亵渎罪,甚至暗示上帝可能是骗子的可能性——似乎不太合理,因为笛卡尔在第一次沉思结束时通过用恶魔代替上帝来表现出对这个问题的敏感性,并且继续论证欺骗上帝的假设包含矛盾笛卡尔是否因拒绝托马斯主义版本的关于上帝存在的宇宙论论证并用他自己不太令人满意的论证取而代之的无神论而犯了无神论之罪——这可能是一个合理的担忧,尽管批评家论证的细节表明对笛卡尔的概念理解很差上帝的观念笛卡尔是否因过度抬举自由意志而犯有伯拉纠主义之罪最后一项指控的主要依据是笛卡尔在第四次沉思中声称,他在自己的内心体验到了一种如此巨大的选择自由,以至于他无法想象更大自由的想法(亚当和坦纳里七世,第 57 页)。最重要的是,由于他的自由,他明白了他是如何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的。
早在 1637 年,在与梅森的通信中就出现了对伯拉纠主义的指责(Adam 和 Tannery I,第 366 页)。笛卡尔一直对此感到困惑,因为他理解伯拉纠的异端邪说涉及这样一种主张,即个人仅使用自己的自然力量,无需特殊的神圣恩典,就可以实现救赎。他知道他从未提出过这种要求,并且在情况需要时他很乐意拒绝(Adam 和 Tannery III,第 544 页)。然而,当莱顿大学的策展人禁止对笛卡尔的观点进行任何讨论,无论是正面还是反面,笛卡尔向他们提出上诉,抱怨必须允许他为自己的虚假陈述辩护时,大学校长很愿意笛卡尔建议他放弃上诉。这件事可能会提交给一个教会委员会,在那里他的反对者肯定会获胜,这不是因为他所说的意志自由,而是“因为他们相信他是伪装的耶稣会士”(Verbeek 1992,第 47 页) . 鉴于笛卡尔在法国与耶稣会士之间的麻烦,这具有讽刺意味,但这并不是笛卡尔关于自由意志的模糊立场所引起的最后一次讽刺,我们将在后面看到。
这些年对笛卡尔来说是忙碌的。困扰他的一件事是看到他的主要拉丁作品被翻译成法语,以便更广泛的读者阅读。很多朋友都做了翻译:Luynes 公爵 Louis Charles dAlbert 做了冥想;Claude Clerselier,反对与答复;和住持克劳德皮科特,原则. 译文于 1647 年出版。在每种情况下,笛卡尔都应该对其进行审查,大概是纠正他发现的任何错误,并偶尔添加文本以更清楚地解释他的观点。原则上,这意味着我们可能更喜欢他作品的法文译本,而不是拉丁文原著。但尚不清楚我们可以对法式变体施加多少权重。我们不知道他是多么仔细地审阅翻译。几乎可以肯定,巨大的变化来自他的手。较小的则值得怀疑。笛卡尔较早的英文译本混合了拉丁文和法文文本。参考书目(Cottingham、Stoothoff、Murdoch 和 Kenny)中列出的现在标准翻译正确地将拉丁文作为主要文本,并指出了法文的变化。
1647 年或 1648 年,笛卡尔与他的前追随者亨利库斯·雷吉乌斯 (Henricus Regius) 发生争执,后者提出了与笛卡尔哲学不一致的立场。笛卡尔首先在他为《原则》的法文翻译所写的序言中批评了雷吉乌斯,后来又在他的短篇作品Notae in programma quoddam 中进行了批评。(关于程序的注释;也称为对某个宽幅纸的评论),出版于 1648 年,以其对笛卡尔关于先天思想的观点的澄清而著称。同样在 1648 年,笛卡尔坐下来与一位名叫弗兰斯·伯曼的年轻荷兰神学学生进行了长时间的访谈。伯曼为采访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仔细阅读了笛卡尔已发表的作品,并提出了有关它们的探索性问题。他对笛卡尔回答的记录是有关笛卡尔观点的宝贵信息来源,尽管有时不清楚伯曼是否准确地抄录了笛卡尔所说的话。
在这一时期即将结束时,笛卡尔与瑞典女王克里斯蒂娜进行了通信,后者将她在斯德哥尔摩的宫廷作为学习中心。他们的大部分通信都是通过法国大使皮埃尔-赫克托·沙努特进行的,没有什么让他与伊丽莎白的通信如此有趣的让步。但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笛卡尔与克里斯蒂娜的关系在其他方面也很重要。
灵魂的激情(1649)
灵魂的激情是笛卡尔最认真的尝试,以提供法文版《原则》序言中所承诺的道德哲学。在一封序言中,笛卡尔说他将“仅作为自然哲学家”来对待激情,而不是“作为修辞学家,甚至作为道德哲学家”。但这有点误导。虽然工作开始于笛卡尔生理学快速场(秒1。- 16),并且强调它们与主体(17秒,25,27紧密连接的喜怒哀乐更宽和更窄的定义。-29),它以对激情的道德评价结束,这更像是亚里士多德的温和而不是斯多葛的严谨:激情在本质上都是好的;我们需要做的就是避免它们的过度使用和滥用(第 211 条)。事实上,今生所有的善恶都只取决于情欲(第 212 节)。
从广义上讲,灵魂的激情是灵魂从它们所代表的事物中获得的感知(第 17 节)。有时,这些感知所代表的事物就在灵魂本身,就像我们感知我们的意志、想象等一样(第 19 节)。有时,它们所代表的事物要么在我们的身体中,要么在一些作用于我们身体的外部物体中。这一类包括身体感觉、外部物体的感觉和狭义的情欲。最后这些被定义为灵魂的兴奋,虽然实际上是由动物精神的某些运动直接引起的,但不被认为具有该近因,而是指灵魂本身(第 27 节)。
笛卡尔坚持认为有六种“简单而原始”的激情:惊奇、爱、恨、欲望、喜悦和悲伤(第 69 节)。所有其他激情要么是原始激情的组合,要么是它们的特定种类。就像感觉一样,激情有助于保持身心结合:它们的使用“仅在于这一点,它们使灵魂倾向于自然告诉我们有用的事物并坚持这种意志”(第 52 节)。它们是大自然告诉我们什么对我们有用什么对我们有害的方式,激励我们追求有用的东西,避免有害的东西。恐惧的感觉激发了逃跑的意愿;大胆的感觉激发了战斗的意志。
动物精神的运动与其引起和维持的灵魂的兴奋之间的联系在这里并不比在与伊丽莎白的通信中更明显。笛卡尔将相互作用的位点确定为松果体,选择这个角色,似乎是因为它是大脑中唯一不是双重的部分,而且因为这个腺体的轻微运动可以极大地改变动物精神的运动相反,动物精神的轻微运动可以极大地改变这个腺体的运动(第 31 - 32 节)。但是松果体的特定运动如何可以影响灵魂以及灵魂的动作如何可以移动松果体是笼罩在沉默中的谜团。显然,这些联系是“天生”建立的(第 44、50 节),也就是说,我们假设是上帝的旨意。
笛卡尔似乎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上帝所设置的规律对我们来说效果很好。但正如在第六禅修中,我们的身体感觉有时会导致我们误入歧途,导致我们想喝酒,例如,当喝酒对我们有害时,我们的情欲有时也会使我们误入歧途。“当我们感到热血沸腾时,我们应该受到警告并记住,一切呈现在想象中的东西都倾向于欺骗灵魂,并使支持其激情对象的理由显得比实际情况强得多,而与之相反的则是原因要弱得多”(第 211 节)。如果激情偏爱一些不需要立即行动的对象,我们应该避免立即做出任何判断,并用其他想法分散自己的注意力,直到我们的血液冷却为止。如果它促使我们采取需要立即采取行动的行动,我们应该反思反对该行动的原因,即使它们看起来较弱,也应遵循它们。笛卡尔说,这是“所有过度激情的一般补救措施,最容易付诸实践”(第 211 节)。笛卡尔在研究道德哲学时并不处于最佳状态。
死亡与定罪 (1649–1663)
1649 年 7 月,应克里斯蒂娜女王的邀请,笛卡尔启程前往斯德哥尔摩,在那里提升她的宫廷作为知识中心的声誉,并为女王提供哲学课程。这次瑞典冒险并没有愉快地结束。当笛卡尔于 10 月首次抵达时,他的职责微乎其微。但到一月中旬,他被要求给克里斯蒂娜上五小时的哲学课,每周三个早上,从早上五点开始。两周之内,他患上了肺炎。到 1650 年 2 月 11 日,他已经去世。
十三年后,笛卡尔的作品被列入天主教会的禁书索引。长期以来,这种谴责的依据是什么还不清楚,但最近信教部的档案馆已经开放,可以更清楚地了解教会的原因和程序。圣所指派了两名外部顾问阅读笛卡尔的作品并对其进行报告:Joannes Tartaglia,阅读方法论(及其论文)和沉思(带有反对和答复);和 Stephanus Spinula,阅读哲学原理和灵魂的激情. 总的来说,审查员(尤其是塔尔塔利亚)似乎做得很仔细,他们只将笛卡尔实际持有的学说归于他,或者至少可以从他所写的内容中合理地推断出这些学说。
审查员发现很多反对意见。有些是笛卡尔物理学中的命题,笛卡尔知道他正在推动正统的界限:否认实体形式和真实性质;地球运动而太阳不动的学说;物理宇宙没有限制的学说。其他的则是笛卡尔认识论的基本学说:作为一个思考的事物的自我的存在是第一个明显的真理,所有其他的明显的真理都来自于它;除非我们清楚地知道上帝存在并且不能欺骗我们,否则我们无法清楚地了解什么是真实的;并且标准的托马斯主义版本的宇宙论论证是证明上帝存在的不令人满意的方式。
特别有趣的是对与人类自由有关的两种学说的反对意见:灵魂可以很容易地获得超越其所有激情的绝对权力;意志的自由并不需要免于必然性的自由,而只需要免于约束的自由。其中第一个是斯宾诺莎在其《伦理学》第五部分的序言中也尖锐批评的命题. 第二个是教会在 1653 年谴责的五个詹森主义主张之一。 因此,尽管荷兰新教徒指责笛卡尔的伯拉纠主义(意志不受罪的束缚,但可以选择善恶的学说),但天主教会谴责他支持詹森主义,也就是说,支持那些认为耶稣会神学家在反对路德宗/加尔文主义否认自由意志的反应中屈服于伯拉纠主义的教会内的人。通向正统教义的大门确实很窄。
版权声明:CosMeDna所有作品(图文、音视频)均由用户自行上传分享,仅供网友学习交流。若您的权利被侵害,请联系删除!
本文链接://www.cosmedna.com/article/356395964.html